2020年12月4日晚9点,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情感帝国主义与近代国际关系史——为什么强权国家也喜欢扮演受害者?”讲谈会通过腾讯会议直播在云端举行。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副教授章可主持,主讲人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与谈人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
陈利老师的报告由两幅极具视觉冲击效果的漫画切入,引出伤害话语(injury discourse)和受害者情结(victim complex)两个概念,指出中澳外交争端背后的实质和历史上的情感帝国主义政治背后的话语政治和国际权力关系有很深渊源和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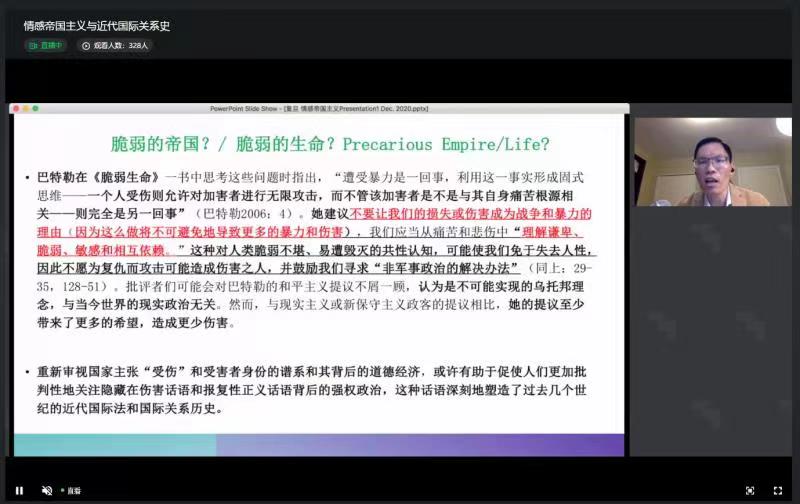
在《帝国眼中的中国法》(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一书的第四章中,他阐述了从情感自由主义(sentimental liberalism)到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十八世纪时期开始,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休谟(David Hume)、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启蒙运动的“巨匠”对认为代表了现代文明社会和个体的情感尤其是同情心(sympathy)的诠释和提倡,使得欧洲情感自由主义的思潮的广泛传播。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继续全球扩张,到19世纪上半期为止,情感自由主义已逐渐蜕变成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在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影响下,中国被刻画成是一个野蛮、残暴、专制和麻木不仁的民族和国家。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和战争行为也被表述成是为了对抗这种所谓的东方野蛮专制政权并把被其奴役的百姓解放出来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
这种情感主义话语又是如何被殖民帝国利用,并同伤害话语相结合的呢?陈老师通过分析耶稣受难像的道德和法理意义指出,对耶稣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以及迫害耶稣之人的残忍邪恶的刻画,反衬出了耶稣及其所代表之所有受害者的善良。因此,受害者身份被用来先验地确立了受害者的道德正义和优越地位。将加害者和受害者形成道德和法理上的二元对立(dichotomization)是解读受害者政治(victim politics)的关键,也是批判性分析报复性暴力行为背后的道德正当性的关键。
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和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等15-17世纪期间的近代西方国际法奠基者们的著作表明,伤害和复仇的理念仍旧是近现代国际法体系中关于一国是否以及何时能够发动合法/正义战争(just war)的逻辑关键。由此产生的关于伤害和正义战争的话语,很大程度上塑造了15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扩张以及之后宏观图景下的国际关系。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等早期近代殖民国家,经常主张其在非基督教世界享有自由贸易、游历和传教等一系列自然权利,为其海外殖民扩张寻找正当理由。在当地遭遇的抵制行使该等“权利”会被解释为对这些殖民国家的伤害,从而成为所谓正义战争的理由。这些强权国家扩张的理由经常不是直接凭借其军事或经济优势,而是通过声称是受害者,变成确保其殖民扩张和征服的最有效手段。除了声称受到直接伤害外,殖民国家还发展一种学简介受害者的理论,即声成对人道/人类部分成员/社会的伤害,也是对(假定)具有同情心和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国家/国民的间接伤害,为后者创造了政治后者武力或者政治干涉的法律权利和道德义务。
情感帝国主义成了帝国扩张的一个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殖民者将同情心和怜悯心政治化以获得向对方推行优越文明的使命感,将那些无法用法律或道德原则来辩解的帝国政策和行径合法化。对不同人群/民族的伤害和是否值得悲痛(Judith Butler’s grievability)作出不同的表述,往往使得强权者能够在损害弱小者利益的情况下操纵伤害话语。陈老师然后用日本和美国为例,分析了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伤害话语”和“受害者政治”是如何在今天继续运行的。澳大利亚空军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残杀无辜平民的背后不仅仅是纪律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暴行所隐含的不把对方当人或者当作平等同类(dehumanizing)的态度和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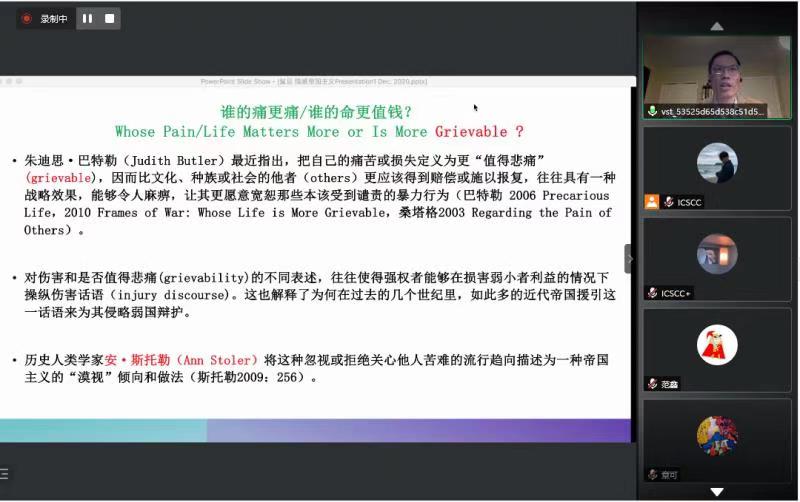
陈老师指出,从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时期到当今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对于那些以受害者身份来使用暴力或者发动掠夺战争并造成更大伤害和暴行的行为,我们都必须以批判性态度来深刻审视这种伤害话语和受害者身份背后的权力政治。要反复思考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有人的苦痛被定义为更值得让人悲痛(more grievable)和报复?谁有资格来决定别人的苦痛或者死亡是否更值得报复?为什么以受害者名义采取的行动反而为造成更多无辜受害者的伤痛和牺牲提供了法律和道德合法性?

在报告的最后,陈老师引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如果一个人拒绝思考,就交出了人类的特质,再也无法作出道德判断。正是这种思考的无能,让人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强调对宏大叙事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重新审视国家主张“受伤”和受害者身份的谱系和道德经济,或许有助于促使人们更加批判性地关注隐藏在伤害话语和报复性正义话语背后的强权政治。陈老师本次讲座的一些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一篇刚译成中文的文章中了(英文原文是The State as Victim: Ethical Politics of Injury Claims and 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jury and Injustic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arm and Redress, eds., Anne Bloom, David Engel, and Michael McCann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7), 293-316),该文章将收入他计划由法律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中文学术论文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后续消息。

与谈人章永乐老师对陈利老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研究聚焦于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具有典范意义,可为研究同时段不平等的跨文化接触与冲突(不仅限于中国和西方)提供启发,并从三个方面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与补充。
首先,他指出澳大利亚政客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回应表示出诧异,这表明了一种优越者情结(superior complex),这是情感帝国主义非常重要的后果。随后,他通过回顾希腊罗马时期的战争理由,肯定陈利教授将受害者话语归因于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的影响的解释进路,但同时也指出基督教传播的内部差异(天主教和新教)对殖民主义阶段性特征的影响以及不同思想家论述因宗教差异带来的分歧。
随后,他从思想史层面对同情(sympathy)概念进行了探讨。维多利亚的论述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关于“人是城邦的动物”或“人是社会的动物”的论述下展开,在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强设定”中,“同情”不可能获得多少理论地位。但经历宗教战争,理论家不断“削薄”人的社会性,在霍布斯这里达到一个最低点。之后的思想家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重建人的社会性,“同情”的“分量”不断被加重。与此同时,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也不容忽视。在近代早期,印刷术普及,报纸与大众媒体兴起,代议制政治进一步发展, “公共舆论影响政治”的现象也日益凸显。18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文明”的概念,将西方内部发生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不断纳入其中,包括酷刑和奴隶制的废除,这成为“情感帝国主义”的基础性条件。章老师同时举了美国排华法案的例子,说明美国本土奴隶制的废除如何影响到美国人对于华工的看法,从而理解“情感帝国主义”发生作用的机制。
最后,章老师表达了对情感帝国主义未来的关切。生活在一个图像和视频的时代,人们极易被图像和视频引发同情心,但这又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使情感变成很容易被操纵的东西。章永乐老师追问:情感帝国主义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在提问环节,主讲人陈利老师就腾讯会议和直播间听众提出的情感民族主义和情感反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表述与现代人道标准建立的关系和情感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做了精彩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