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晚7点,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书法史与文化史之间——以《集王圣教序》为中心”的学者讲谈会,讲谈会通过腾讯会议直播在云端举行,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教授主持。

意大利那波利东方大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的开讲主题为《关于<集王圣教序>的研究方法》。毕罗回顾了自己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访学经历和《集王圣教序》的研究缘起。他认为研究艺术品首先要学会如何欣赏艺术品,《集王圣教序》本身是一幅高级的书法作品和艺术品,笔势和笔法局部处理得精致而微妙,如“牵丝”、“银钩”、“虿尾”等,这说明当时对书法作品的审美要求极高。因此,研究书法作品要求研究者必须细致读帖、临帖。对于《集王圣教序》的研究范围和材料,毕罗认为: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关涉其中:信奉道教的书圣王羲之,宣传佛教的高僧玄奘,文武兼备的皇帝李世民。因此,《集王圣教序》不仅会涉及到书法史,也会涉及到宗教史、宫廷史以及政教历史方面的问题。在研究材料上,不仅会涉及到书法领域的相关文献,也会涉及到《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等,这些文献虽然和书法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作为当时的原始资料,还是能找到很多线索。《集王圣教序》的另一个特点,是附有《心经》。这使得研究离不开写本文化和写本研究,这对我们理解碑刻上的历史脉络极有帮助。紧接着,毕罗谈到书法研究离不开逐字分析,书法作品首先是文本作品,只要连笔不夸张的书法作品都可以以汉字作为它的基本单元。当时的很多墓志和碑刻都会打格,行列规划的很清楚。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还特别强调《集王圣教序》的具体字数,与这种情况类似,英藏的《莲华经》也如此,这说明当时的佛经抄写是非常严格的事情。书法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诸如绘画和雕塑的区别,其特点是以汉字为基本单元,这与音乐类似,书法作品中的汉字与音乐理论中的小节和乐句有相似之处。确定汉字在书法作品中的位置,实际上等于确定我们针对的研究对象,类似于笛卡尔的直角坐标系,便于我们找到研究对象的准确位置。做逐字分析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以怎样的底本为统计对象。毕罗学者整理出了《集王圣教序》中的所有汉字,所有偏旁和不同字形。因此,虽然我们对于毛笔书写和书法作品不如古人敏感,但我们仍有路径开启研究。毕罗基于自己复旦大学访学的研究成果撰写了若干篇学术论文与一部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史睿的讲题为《弘福寺的地位与<圣教序>碑的建立》。史睿从地理文化角度梳理了唐玄奘的西游历程、隋唐佛教义学地理变迁以及唐初皇位传递与长安佛寺的关系等问题。同时,结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大慈恩寺碑》制作史,可以看出玄奘在高宗显庆元年至麟德元年的政治斗争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弘福寺的衰落。这对《集王圣教序》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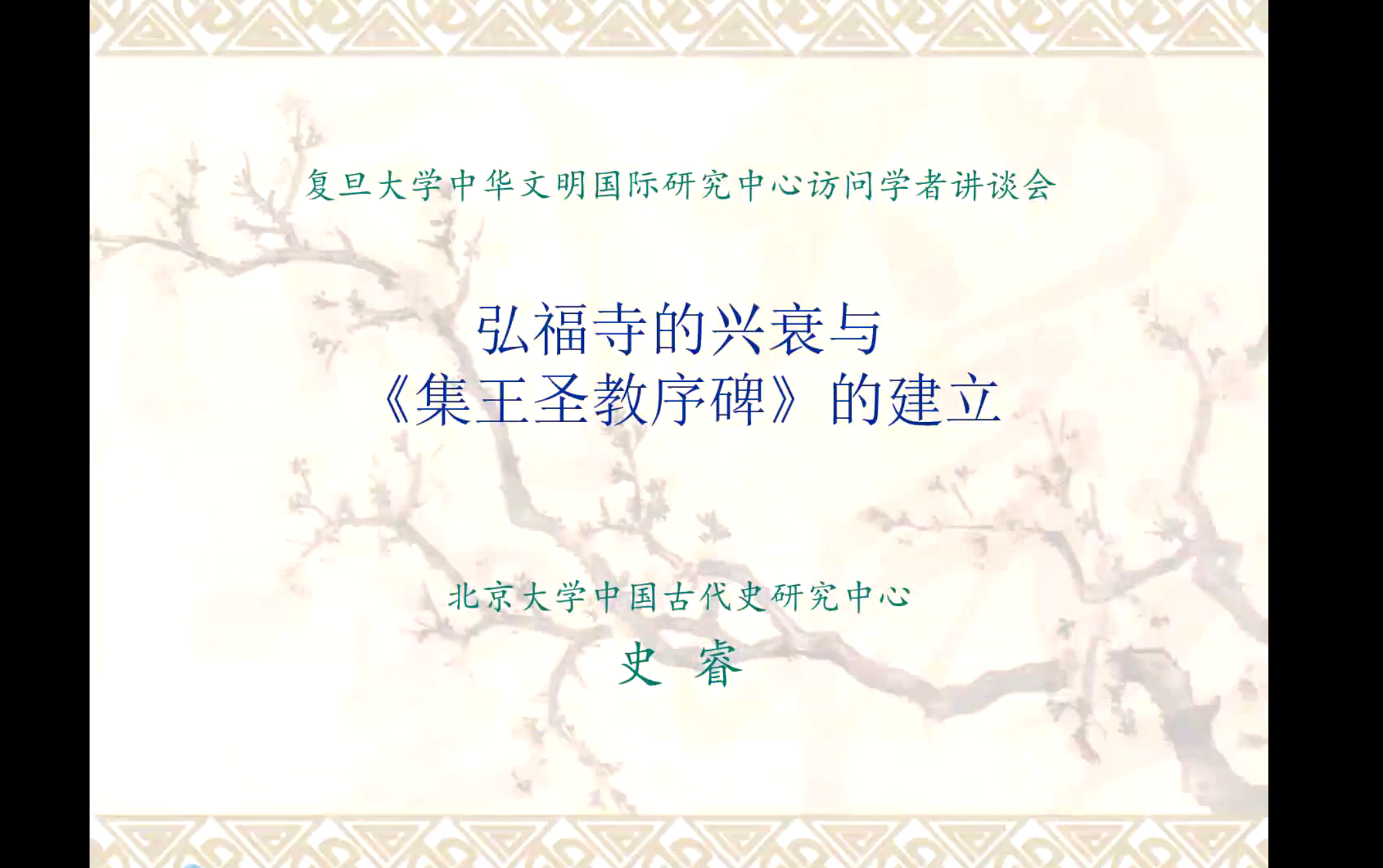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叶康宁的讲题为《近年来<集王圣教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叶康宁介绍了《集王圣教序》拓本的发掘和研究历史。其中,出版最多也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墨皇本”,而孙宝文编老碑帖系列收集了其他十种版本。叶康宁进一步强调了“考据点”的重要性,“考据点”一般指碑刻中变化较大的文字和点画,这些地方就是拓本断代的参照点。根据印本研究拓本,会有很多陷阱,拓本的填描,印本很难看出来。不能接触到大量拓本的研究者,尽可能不要自以为是地寻找新的考据点。除此之外,叶康宁还梳理了近年来《集王圣教序》的相关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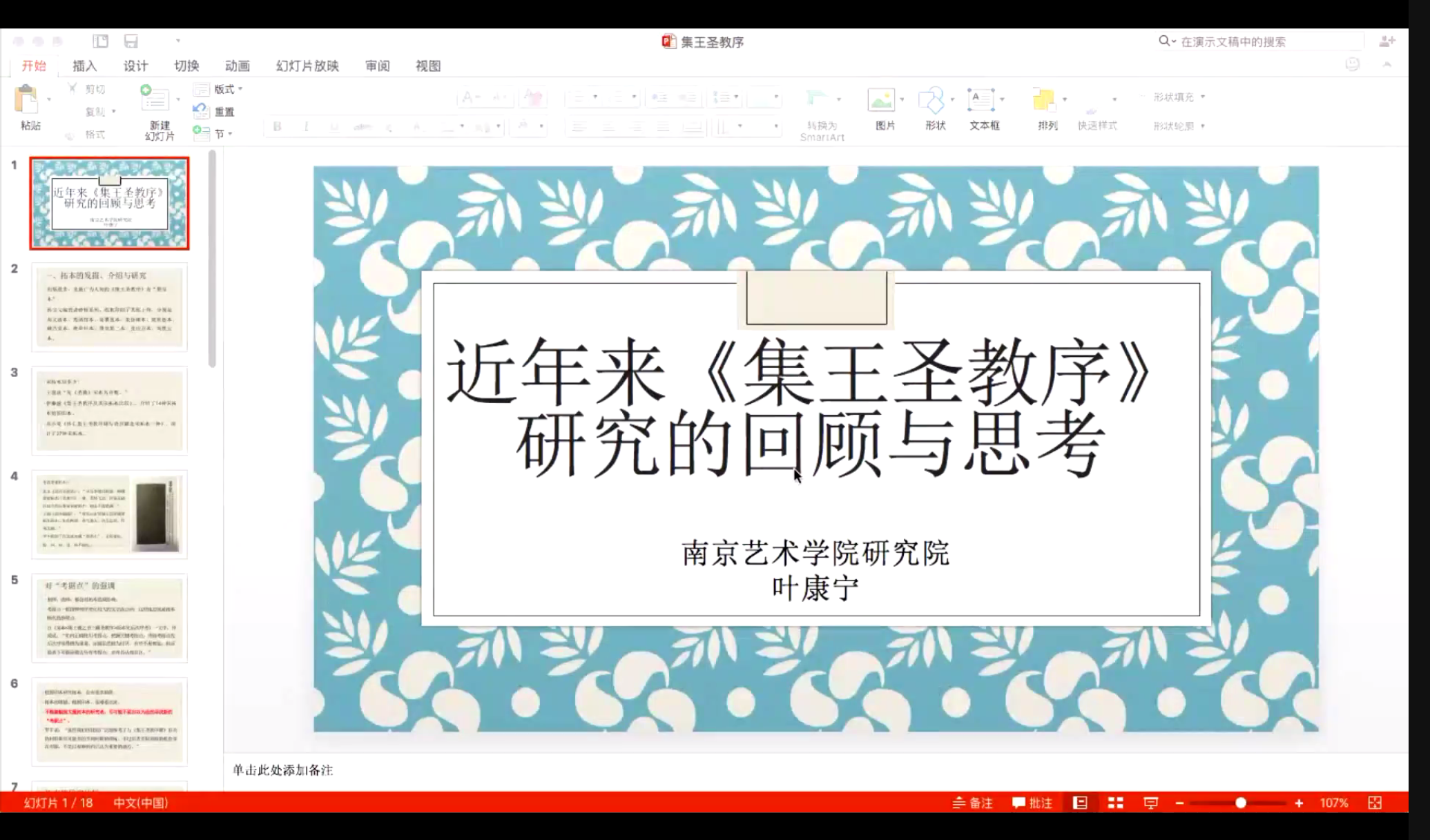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顾毅的讲题为《书法文献的英译现状与中国书法的传播问题》。顾毅分析了不同时期书论典籍的翻译状况以及不同译本的特点,结论是:中国书法已成为一个国际学术话题,研究中国书法的汉学家可以不以翻译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工作离不开翻译。顾毅进一步谈到中国书法文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对比《书谱》三个英译本(孙大雨本、张充和傅汉思本、毕罗本)中使用到的不同副文本形式,顾毅认为学术型的深度翻译应做到:通过评注、注释等副文本形式将古今文献勾连起来,搭建古今文本的互文关系,以使读者对研究对象有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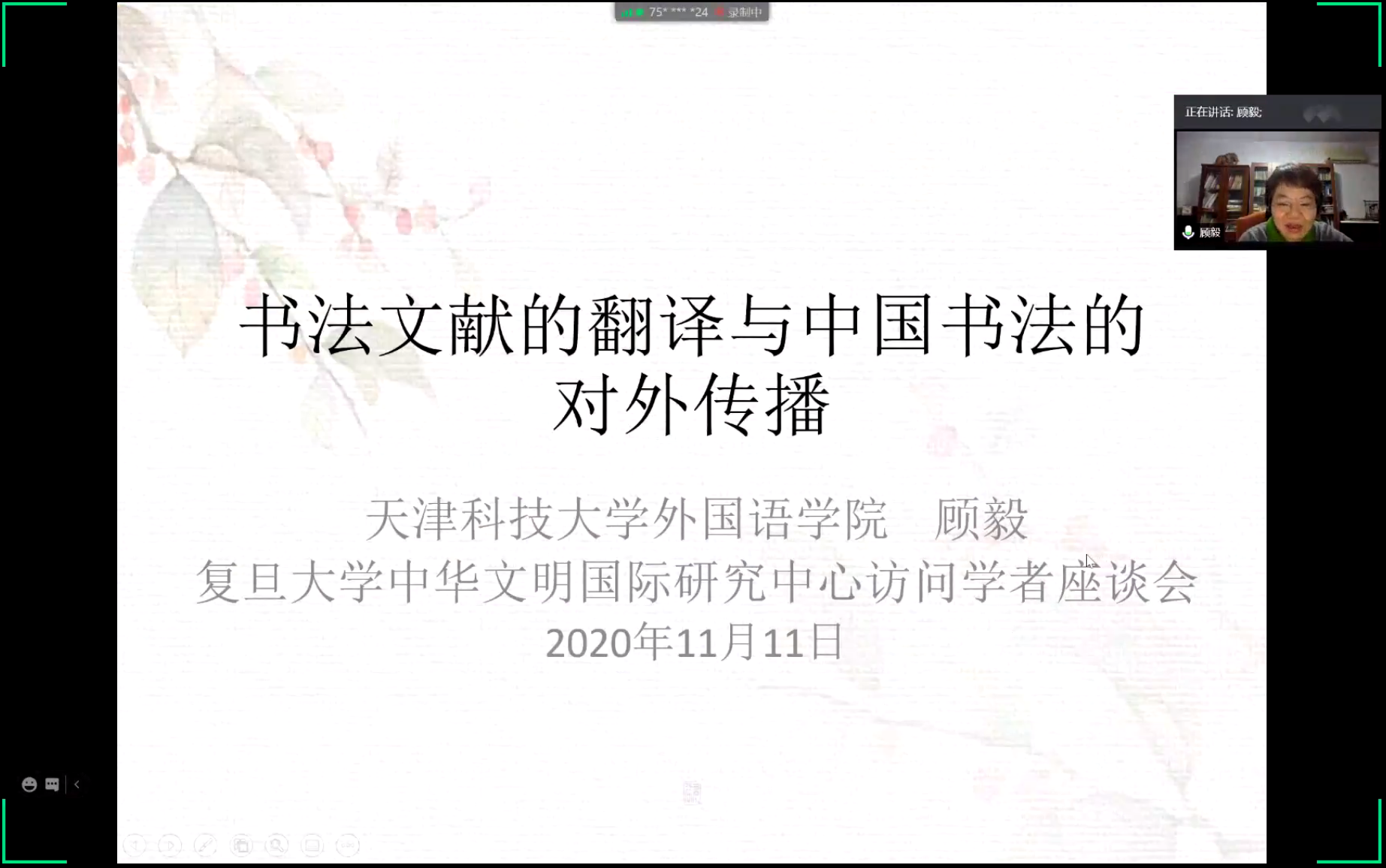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主任封龙的讲题为《<尊右军以翼圣教>编制的始末与出版意义》。封龙认为,此书的旨趣在于呈现从艺术走向历史的研究趋势、艺术史研究的事实与视角以及成一家之言的阶段性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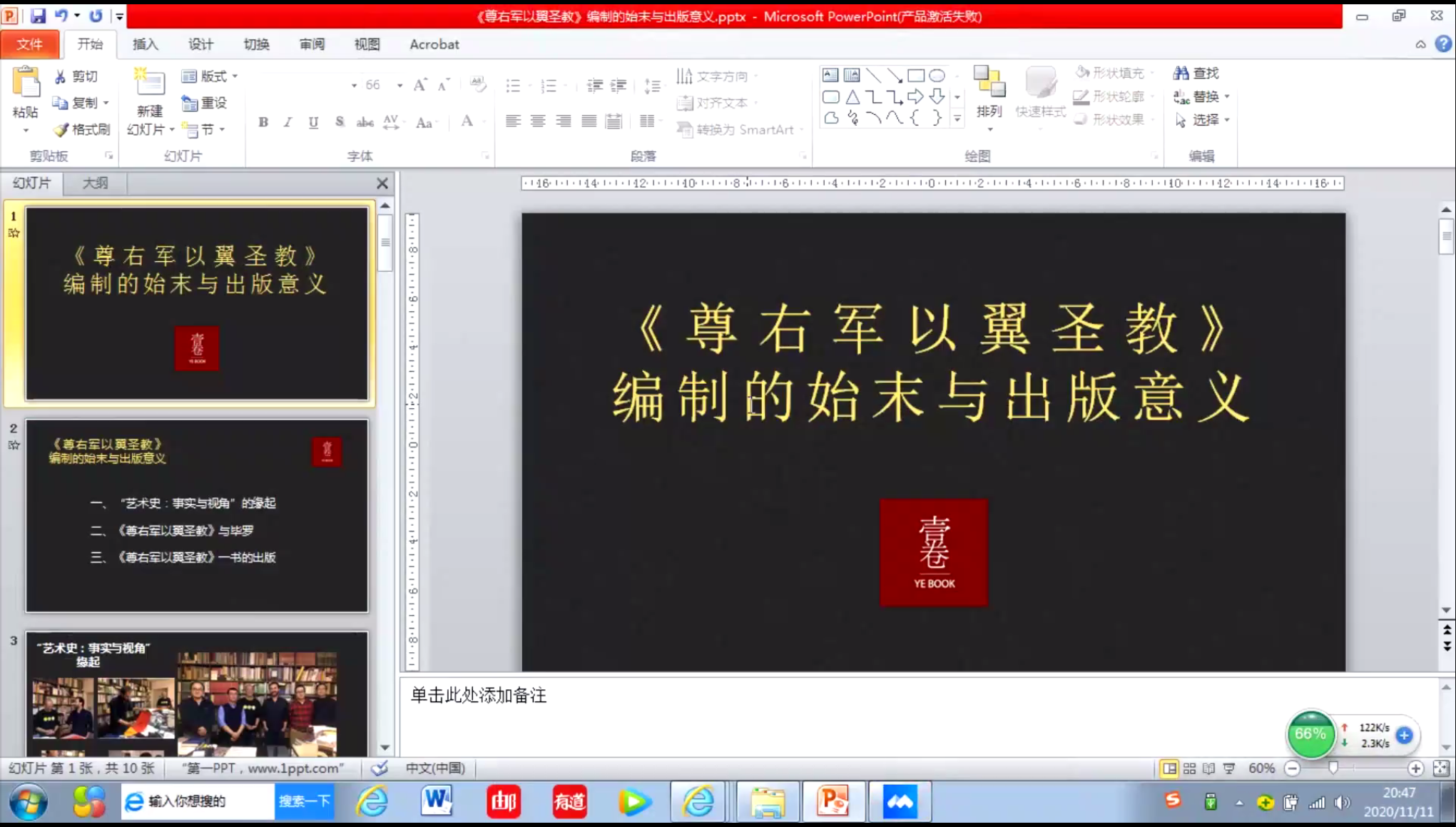
最后各位学者对听众的提问进行了回答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