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2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翻译:文化转移的古与今”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并通过腾讯会议同步直播。
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系陈引驰教授召集,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陶磊博士、王柏华教授、段怀清教授、郜元宝教授、戴从容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共同参加。讲坛会首先由陈引驰教授发表引言。陈老师对本中心的宗旨及此前活动做了简要介绍,并对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到来表示欢迎。

第一组报告的主题为“古代经典译入与译出”。首先,陶磊老师发表了题为《汉文佛典中的译论文献及其研究》的报告。陶老师首先对古代佛经翻译方法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回顾,认为梁启超1920年写作的《翻译文学与佛典》在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后学者对佛经翻译方法的研究基本上承袭了梁启超的论述模式,围绕“直译”“意译”展开。随后,陶老师介绍了汉文佛典译论文献的整理情况,包括1984年罗新璋辑录的《翻译论集》(2009年修订)和2006年朱志瑜、朱晓农出版的《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但二者均篇幅都不大,且主要为佛经序跋和僧传摘录,来源较为单一。而翻译学界对佛经翻译理论的研究主要依赖《翻译论集》,这就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严重局限。对此,陶老师提出两个新的观察对象:首先,他认为除了“五种不翻”之外,玄奘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正翻”和“义翻”这两种佛经翻译方法;此外,唐代澄观提出的“会意译”与“敌对翻”以及他对译经的评价也值得重视。陈引驰老师对汉译佛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汉译佛经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翻译文本的来源和语言问题,哪怕学者具有梵语和胡语的能力,能看到的文本时代不定,且它们所各自属于的传统也是不同的。第二,从翻译过程来看,目前对“笔受”的重视不够。第三,到底什么叫敌对译、会意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随后,王柏华老师发表了题为《中国古典诗词外译的几个误区》的报告。王老师表示,自己近年来主要从事英诗研究和翻译,同时一直关注中国诗歌的外译,其实二者是相通的。她赞同本雅明为诗歌创造来生(afterlife)的观点,以及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的交际功能:让译本与当代读者交流。因此,王老师强调,为古典诗词创造来生的策略多种多样,译者需要从整体上思考,好诗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古诗的独特品质究竟是什么?它能够贡献于世界、为当代读者所欣赏、所继承的东西究竟什么?Kenneth Rexroth早就指出,中国诗歌的法则是呈现出具体可感的“诗的情境”(Poetic situation),邀请读者置身其中;宇文所安认为中国盛唐诗的特色是心理上的微妙细腻,简朴的语言和丰富的言外之意。这些才是在译作中最不应该丢掉的东西,而死守格律可能是最次要的、最低级的策略,而且总是得不偿失。王老师指出,自从英美新诗运动以来,无论汉学家还是诗人译者,都没有死守格律,而是采用自由体和鲜活的当代语言,着力于用新的语言和音乐形式创造同样的意境,因此都成功避免了俗滥的韵脚、颠倒词序、堆砌古语或诗语(Poetic diction)、随意增删等早期译家的各种弊病。显然,一大批国内译者仍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旧时代,似乎对当代诗学一无所知。而且,王老师发现,很多译者对传统英诗格律有一种误解,事实上传统英诗虽讲究格律,但大诗人的诗作都不是匠人之作,他们擅于动用各种音韵手段(如头韵、腹韵、跨行等),打破音步和韵脚造成的束缚,让诗作具有灵活多变的散文化风格。不客气地说,很多活跃在中国当代的古诗译者(在盲目的民族主义和不知情的读者的吹捧下,在商业利益的推动下,享受着极高的赞誉,而且催生出无数学术垃圾),不过费力不讨好地制造出一些古怪生硬的蹩脚的匠人之作,更有甚者,不过是一堆粗制滥造的打油诗,根本无法实现中国古诗与当代读者的交流,更无法走向世界(事实上很多译作都是自产自销)。因此,王老师总结说,中国古典诗词的译者要对西诗有深入的理解,与当代诗学保持同步,才能使中诗外译和当代读者发生共鸣,实现交流功能。陈引驰老师评议:诗歌翻译的目标、和读者对象确实很重要。译入语系统决定了一个翻译是否成功。如彭斯(Robert Burns)的A Red Red Rose写海枯石烂,在英文诗歌中是很惊人的,但是在熟悉中国传统、读过《上邪》的人读来觉得没有什么新奇,如何让中国读者能够欣赏它,这就是挑战。并且好的翻译要对两种语言都有风格学、文体学的了解。
第二组讲谈以“西学翻译文献与模式”为主题。邹振环老师从研究方法入手,做了以《西学翻译文献学刍议》为题的报告。邹振环老师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方法运用到翻译文献当中,借用传统文献学研究所涉及的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的范围和方法,提出对西学汉译文献学的新认识。在定位西学汉译文献时,邹老师认为中国的翻译史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西学汉译”三个阶段, 其中西学汉译文献,和传统文献比有什么特点?它属于一种用汉文翻译异域的新文献,这些新文献有以下特点:首先,它具有跨文化、跨语境、跨时代的多元性特征;其次,它犹如佛典翻译,虽用汉文表达,但多由中外两国学者的口译和笔述的合作。邹老师认为西学翻译文献学第一编为“西学汉译版本学”,可以分为“一、西学汉译文献的写本与刊本”、“二、西学汉译文献的官刊、私刊、坊刊和堂院刊本”、“三、西学汉译文献的删编本和评注本”三个方向展开研究。第二编为“西学汉译文献校勘学”,可以分为“译本的原本来源考订”、“同一原本之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同一译本初版和再版的修改”、“书名的异译”、“专有名词的异译”、“人名、地名的异译”进行研究。第三编为“西学汉译目录学”,包括“西学译书目录的两种体例(综合目录中的西学汉译书目和作为特殊目录的译书目录)”、“民营书局书目”、“私家修撰目录”等方向。陈引驰老师认为,对西学汉译文献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西学汉译之历史过程,更是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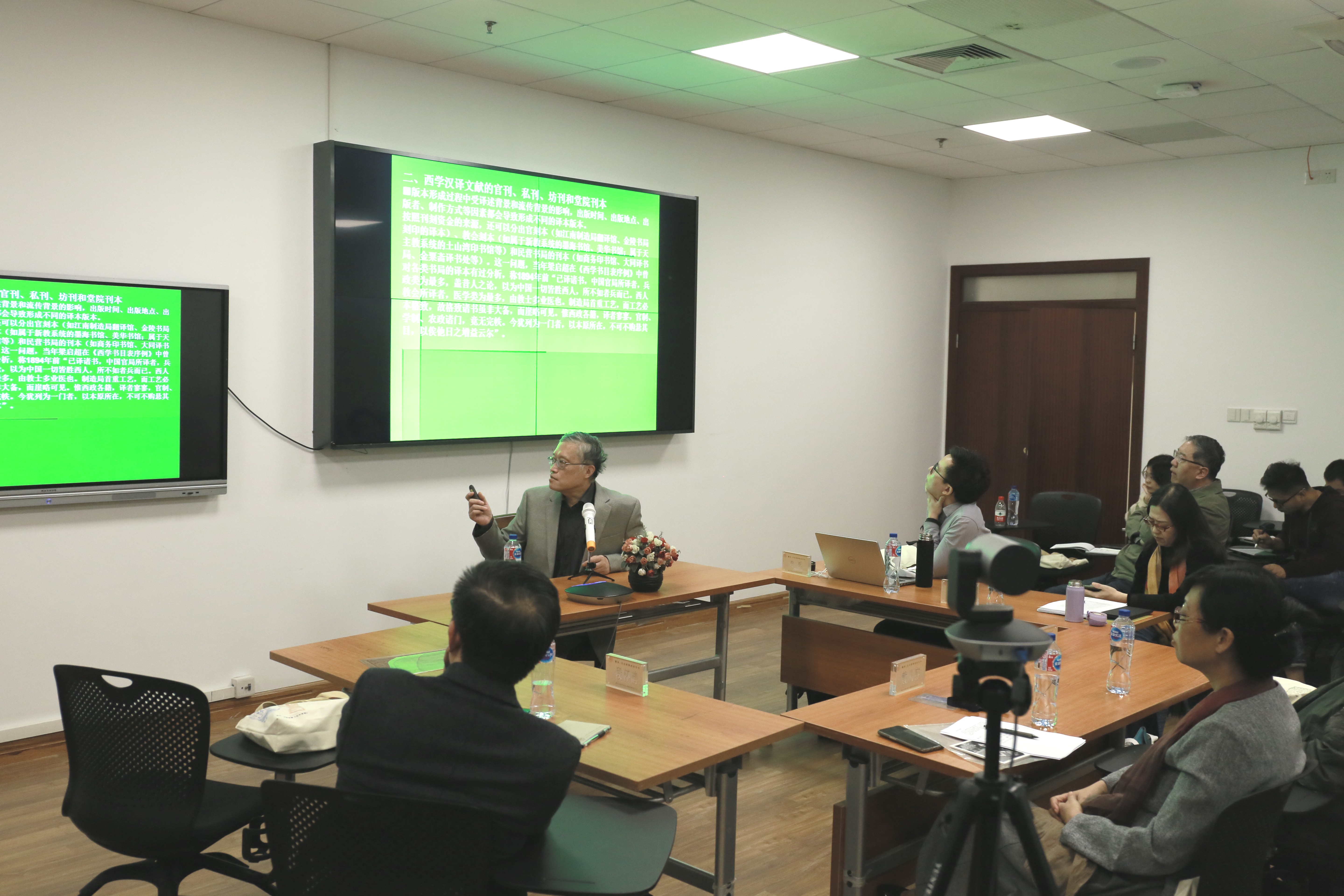
段怀清老师就《晚清的国家翻译与私人翻译——兼及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发表报告。段老师指出,在研究晚清翻译理论时,一旦深入到译者的个案中,关注翻译的故事和细节时,就会发现翻译策略中的技术、语言、修辞的考量,实际上往往还关涉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亦就是“译者安全”与“译本安全”的问题。在晚清翻译史上,上述课题在国家翻译层面以及私人翻译领域均存在,而在私人翻译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亦更为常见。不过,晚清的私人翻译与国家翻译又是彼此共存的,也可以说,晚清的私人翻译,亦是与时代更大的翻译背景密不可分的。段老师首先介绍了明清两朝的国家翻译制度:朝贡体制中的四夷馆/四译馆,以及国家垄断翻译,以来来揭示在这种知识制度与翻译体制中,国家翻译与私人翻译之间所存在着的各种微妙关系。随后,段老师介绍了晚清“西学东渐”以及跨语际、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的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局、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等国家机构。此后,段老师认为1840年代之后,很多新现象开始出现,最重要的就是开埠口岸的出现,出现了私人翻译与晚清的知识/思想解放与革命,导致晚清知识、出版及传播的市场化与私人翻译的快速发展。相比而言,国家主导的翻译,推动了整个时代的外来知识的制度化“普及”,但却较少产生对同时代或后代的思想解放发挥巨大影响力和促进作用的文本;而恰恰是晚清的私人翻译及其成就却影响深远。因此,晚清的国家翻译与私人翻译之间既持续博弈,相互依托映衬,亦出现了分野与专司的现象。段老师认为,晚清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主体、译者权力与译者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如果翻检晚清译者的署名方式,多见“口译-笔述”这样一种组合式翻译模式。而无论是由来华传教士发起并主导的“口译——笔述”翻译,还是本土文人发起并主导的口译——笔述翻译,其中均存在着“口译”者与“笔述”者之间的权力互动与博弈。涉及到翻译内容的选择,以及译者身份、地位、职能的分工,这些在译本的署名方式中亦多有呈现。以严复为例,在翻译过程中他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不确定所翻译的文本思想,在当时的语境中产生来自政治、主流社会、官方反馈的可能性的预测和判断。我们看得到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用先秦名词去翻译,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是他通过这个方式,去构建一种能够相对安全保险地和一个正处于风云激荡、变革声起时代进行对话的系统机制。陈引驰老师认为,翻译过程中文本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离开支撑起文本生成的更为复杂的背景讨论。因此段老师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组报告以“现当代文学之译与写”为主题。首先是郜元宝老师以《鲁迅译介与<野草>》为题发表报告。郜老师认为,学界向来将《野草》之难读归因于鲁迅的文学才华,而郜老师关注了《野草》中的潜文本,并将其分为三类:其一,和《野草》互文的鲁迅“创作”;其二,和《野草》互文的鲁迅本人所译介、鲁迅引他人所译介(佛典)等;其三,与《野草》互文的其他文本(鲁迅提及、或明或暗引用他人作品,“关系人”的回忆与论述),以上这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研究思路借鉴了古代文学引书研究的方法。从这一思路出发,可以尝试解决《野草》的许多问题。第一,是野草得名的问题:日本学者秋吉收认为《野草》是讽刺成仿吾,但郜老师认为这也应该考虑是因为鲁迅读过(甚至以转述内容的方式译介过)《哈泽穆拉特》;第二,关于《野草·题辞》《影的告别》《墓碣文》中的“死尸”“朽腐”“黄金世界”等用词,或来自《工人绥惠略夫》,具有连锁关系。第三,《野草》的创作和《小约翰》的翻译有密切的关系,如《小约翰》全书写梦,野草也多写梦,并且有诸如“奇怪而高的天空”等特殊的语词细节是可以落实的。第四,《影的告别》写“形影对话”(其实是影的独白)除了源于鲁迅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斯忒拉》所批评的灵魂对肉体的蔑视,也可能与鲁迅在《工人绥惠略夫》译后记中说这是“内心的交争”有关。此外如《墓碣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意象,可能来自鲁迅所翻译安特来夫《谩》;《颓败线的颤动》文本内部无法解释“颓败线”,但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颓败的肌肉线”可能提供阐释,以及本篇开头描写老妇年轻时为养活家人而卖淫的“肉欲”成分,也来自《工人绥惠略夫》。

最后,戴从容老师发表了《当代爱尔兰文学翻译模式的变化:以詹姆斯·乔伊斯为例》的报告。戴老师从乔伊斯的翻译史入手,从个案分析为何爱尔兰文学引起中国学界的兴趣。戴老师通过比较解放前的乔伊斯翻译介绍和80年代后对乔伊斯的翻译和介绍,指出解放前的翻译主要呈现出译者主导的特点。通过分析对乔伊斯的关注所集中的各个时间点,戴老师指出早期的翻译研究具有受新闻影响和受译者影响的特点,翻译所选择的并不是乔伊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是译者自己的爱好和判断。80年代之后,在袁可嘉先生的推动下,翻译和研究取得较高成就,但之后渐渐出现了陈德鸿提出的翻译的商品化的现象,即出版社的宣传和营销手段在翻译中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图书出版公司甚至取消了译者的名字,翻译从精英模式已经变成出版社商业竞争的丛林模式。另一方面,更多赞助人因素进入翻译,如政府行为。爱尔兰政府对爱尔兰文化外译的推动力度非常大,并且通过向中国有关的学者、出版社、机构大量宣传爱尔兰的作家和文学,从而推动爱尔兰的翻译和研究。戴老师认为,在如何让翻译走上更加良性的发展问题上,她比较欣赏的是译者和赞助人达到更加平衡互补的模式。陈引驰老师认为,这个问题从个案入手,又涉及了翻译周围的各种问题,对我们非常有参考价值。

最后一个环节是讨论和互动。段怀清老师认为,郜元宝老师的文献信息、分析思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改变了他曾认为鲁迅作品中的一些表述方式是鲁迅个人修辞的独创的想法,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鲁迅创作型书写和翻译之间,翻译和写作的风格、主题、语言之间构成了对话性的内涵。有一些句子,在译本和创作中用两种不同的风格来表达意象,我不知道这是出于鲁迅有意识地在遮蔽语言的来源,还是在创作和翻译中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目前看来似乎在创作中汉语的主体性更充分一些。郜老师作出回应,表示鲁迅的翻译是比创作要生硬的。陶磊老师也表示,现在很多作家都是既创作又翻译,但学界对此往往是从思想性上进行比对,此前没有看到过类似语文学上的研究,能够把这种关联性具体落实到字词上,非常有说服力。
此后,来自翻译系的同学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时期、国籍的翻译是非常不同的,这应和译者主体是有关系的,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现象和译者的关系。段老师回应表示:要结合具体的个案和语境,这是可以抽象谈的问题,但又必须回到个案和经验当中。比如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时,译注部分要远远超出正文的翻译。对此有各种讨论维度,但其中有一个事实:理雅各自己说他只是为了百分之一的人翻译,而不是99%。由此出发,结合理雅各个人的语境,如他和牛津的关系、翻译学术性与他译者身份的关系,就可以综合地区考虑译本的特质,而非仅仅考虑翻译本身的策略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