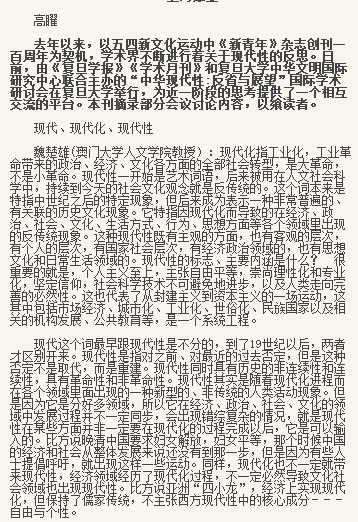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实用了“现代”一词。
现代性的特殊性、差异性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中华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我们任何的言说背后都有全球化的背景。我们基本主张是这样的,世界各大文明体独立的发展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个对话的时代。怎么样促进对话?如果真的承认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的,未来就应该是多元模式的相互对话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竞、视野的交融和知识共同体的催生。
我想讨论的是知识共同体中的现代性。要建成这种知识共同体,有许多问题要梳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现代性就是其中一个。和罗马社会相区别,归于基督教的社会,古代和现代的区别有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它崇尚理性;第二个特点是,能代替一些超越性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三是分门化的确立。这些特征进入中国,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些特点,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就像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后发的,中国的后发的现代性本身能不能持续,能走多远?成为一种问题。中国的现代性展开过程当中始终伴随着深深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我们肯定现代性,甚至张开双臂拥抱现代性;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深深怀疑,甚至反抗。疑虑、反抗、怀疑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
究竟如何在知识共同体的背景下理解并且尊重现代性? 怎样理解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怎样认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落实到中国的语境,怎样认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冲突? 怎样认识中国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未完成性? 怎样在坚持启蒙的同时拒绝后殖民主义理论? 要基于历史的逻辑,又离不开人们的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了30多年,我们眼界也开了。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的观察有许多来自前见。前见是合理的,但许多也片面化了,成为了偏见,所以又的确有许多误判。怎么样真正地发现中国?中国怎么样真正地说明自己?这些都是问题,我想,在此过程中,中西方最好都不要太固执于自己的判断,还是要回归到知识的平台中去。
高瑞泉:我想谈的是“未完成的中国的现代性”,这个题目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尚在途中,也意味着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是有疑问的。中国人希望不希望达到,这也是有严重分歧的,特别表现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经验做概念化的时候,现在比较主流的话语是更强调民族性。这多少也解释了现代性研究最近若干年比较沉寂。和上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相比,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闹。这是我讲的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第一个意义。
第二点,我在合理性的诸形式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我们承认有多元现代性,或者多重多现代性,多元和多重有点不一样,这两个提法还可以分析。但是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一开始都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多元现代性或者多重现代性的提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的现代性的提法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假如不承认现代性是多元的,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其实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关于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的观念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最初从西欧、北美扩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演化成一个单一的现代性,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历史的现实。但是如果从合理性的诸形式这个角度,我们又要承认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只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特殊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因为有特殊的传统与国际环境而可以呈现为不同的概念化。中国的现代性不过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所作的概念化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状态而生成的。
第三点,关于依照合理性的诸形式来理解现代性的路径,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终究还是现代性,这个说法我比较多的接受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一本书《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它的背景和韦伯、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有关。在那本书里,他把合理性理解为基于行动的,从而也是置身于历史行动和建制当中的。他把诸种合理性分为三种。以往韦伯讲的合理性就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的非常强烈的冲突。按照希尔贝克的说法,把合理性分为工具合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论辩的合理性。在那本书里,他把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性作为历史的概念化,而且他说,19到20世纪,基于特殊的时节,民众运动及其精英让工具合理性、解释合适性、论辨合理性以相融合的方式促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到达丹麦,指北欧是我们另一个理想。曾经我们是要到达美国,但现在美国有那么多问题,而北欧把福利国家、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结合得那么好。希尔贝克所说的,一方面现代性是合理性的诸形式,但他的核心是诸种合理性的融合。所以现在说到达丹麦,大约我们是将中国的现代化指向了诸种合理性的融合,而不是合理性的分裂和紧张。那么,当我说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远远没有达到诸种合理性的和谐。我们的工具合理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价值合理性的问题很严重,论辩合理性也有很大缺失。
许纪霖:现代性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华、中国又是特殊的,这里面就有一种特殊的普遍,这是很有意味的问题。我们今天终于和80年代有了最大区别,80年代中国要向西方看齐,追求的是普遍性。现在风水轮流转,要在一个所谓多元的现代性里面寻找中国特殊性,这里面就有一种紧张。
去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0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我们都称为历史自觉、文化自觉。但这个文化自觉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自觉? 因为文化自觉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要走普遍的道路,我把它称为文明的自觉,另一种自觉是说我们要追求特殊的道路,我把它称为文化的自觉。我基本的一个分析就是,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最大的纠结和焦虑就是在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紧张。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最早意识到紧张的是19世纪的德国,因为19世纪德国相比较法国和英国是落后的,他们一方面产生了文明的自觉,要学习法国,法国代表着文明。另一方面,拿破仑入侵以后,德国又试图用特殊的文化对抗法国所代表的文明。就使得19世纪德国同时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自觉。
在历史上,因为我们比周边国家的文化都要高,所以中华文化同时就是中华文明。如果韩国人说韩国文明,是蛮奇怪的,普遍性的文明他们没有贡献过。但是这样一种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合一,到了1840年以后,受到了冲击。中国碰到西洋文明,实力比我们强,文明比我们高级。晚清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文明和文化断裂,晚清以后的保守主义底气已经弱了很多,只讲要守护特殊的文化,而不敢再自称我们依然是对全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文明。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中国要学西方,学的主要是西方的“富强”。把富强看作是最重要的。这是受到社会达文主义推动,用我的话说是富强压倒了文明。但是这样一种思潮到了1914、1915年发生了变化,特别到1917年这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文明有问题,所以开始对以富强为中心的这样一套观念有一些反思,意识到光讲富强不行,还得思考最终的一套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五四时期有启蒙和保守的各种争论。争论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变化,讨论的是世界文明的方向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恰恰又和中国自身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传统一直是天下的传统。五四的潮流基本上还是文明的自觉。到了“九一八”,思想的整个风气发生变化,要救亡,要自身的民族意识。这时候所谓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慢慢有了空间。
中华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就是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的紧张,这是至今没有被解开的困境。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是撕裂的,现代性和中华性也是撕裂的。下一个百年能不能重新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思考的。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五四肯定是作为我们一个现代性的开端,中国的现代性、科学民主价值体系都应该是从五四开始的。欧洲学者已经把现代性推到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有一个长长的序列,有一个现代性的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国有没有呢? 我觉得,至少从中西交往来讲,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现代性。另外,如果更加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去,可以看看我们有没有一种内生的现代性。我觉得五四以来我们的现代性中有这个缺陷。这要回到利玛窦以来的中国文明主义。欧洲在17到19世纪的时候,认为中国是个现代国家,因为中国的世俗主义、人文主义,所以中国是现代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是早就有文艺复兴了。西方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一个具有早期现代性的国家。徐光启提出一个更好的观点,他提出回到汉学,接通西学。这个想法在我们现代性的讨论中应该被提出来,中国的现代是从明末就开始了的。
另外一点看法是,我们在讨论区域性的问题时,中华现代性只是一个相对的划分。我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有一个东亚的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日本、韩国现在应该说都是现代国家了,但是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中有没有共享的现代性呢? 以前儒学、佛学、道家在中日韩都有传播,是东亚共享的,那么今天的东亚有没有一些共享的现代性的价值?我个人是认为,讨论中华的现代性,需要我们从更广的范围来讨论,然后建立学术共同体,来反省我们所经历的100多年,以及更早以前的历史。
原文链接:http://whb.cn/xueren/711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