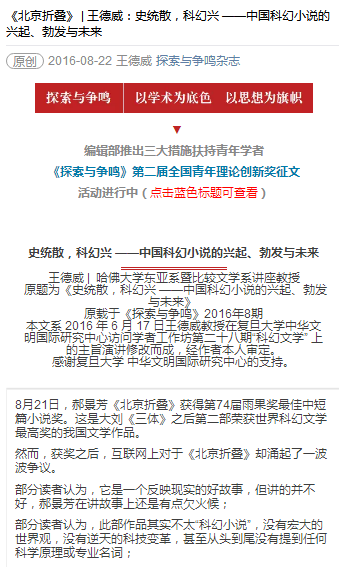我以“史统散,科幻兴”作为起点,其实渊源来自明清文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史统散而小说兴”说法。17世纪上半叶,晚明末期的中国传统白话文小说的重要作家以及编撰者冯梦龙有感世事纷纭、历史动荡,认为当史统不再是人们判断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小说反而取而代之,成为看待古往今来、衡量人世变动的重要源头。冯梦龙写下他的感叹,其实仍是借小说表达对道统的寄托,但无形中也为小说打开了方便之门。“史统散而小说兴”观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晚清时代又出现了另外一波建设,那就是晚清小说的兴起。
我们都知道,晚清小说和当时政治以及其后的历史现象息息相关。而在晚清各种文类中,科幻小说尤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在1980~1990年代阅读了大量晚清科幻小说,也以文字表达过我个人对于这些小说的观察。所以,今天用三个方式说明我的看法。第一,我想做一个双重回顾:从幻想/传奇和写实/现实的辩证关系谈现代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从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的辩证关系谈现代中国小说愿景的转化。第二,我对当代科幻小说做出三点观察:历史政治语言的塑造,认识论和情动力的启动,以及后人类的想象。第三,我个人对科幻小说的过去和未来作出认识和提议;尤其相对耳熟能详的忧患意识的提法,着重发掘科幻小说人性与宇宙“幽暗意识”的能量。
1 双重回顾:科幻何以出现政治潜意识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晚清政局动荡、历史纷扰的时候,各种各样小说文类同时兴起。无论是谴责或是狎邪,无论是公案或是官场,这些小说捕捉到林林总总的现实现象,也对中国的现代性何去何从提出了最精彩甚至是最惊心动魄的观察。在这许多文类里面,我个人以为科幻文类独树一帜,它是晚清小说文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这一贡献却在五四以后的传统中逐渐被淹没了。 诚如陈思和教授所提到的,当现实主义以及写实主义成为新文学的主流,科幻所铺演的各种奇幻的空间以及时间的 想象,各种可能与不可能的人生境况,基本上被存而不论。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奇幻想象和现实主义的对立是一种非常武断、简单的对立。如韩松先生所说,其实我们生存的现实往往比科幻更科幻。的确,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现实场域如此不可思议,也许不再需要科幻小说作家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所谓更超现实的时空里。比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世界迎来了第六座迪士尼乐园。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众多童话人物的簇拥之下,我们展开又一段欢乐奇幻之旅。但也就是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的同时,当一家三口正在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里的河边散步时,突然从河里跳出了一条大鳄鱼,把两岁的小孩拖进了河里,两天之后才发现尸体。我们看到的迪士尼世界真的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回到最纯真、最童真的欢乐的奇幻世界吗?我们的迪士尼世界是不是永远隐藏一条看不见的大鳄鱼,随时准备扑出来毁灭我们对于世界最童真、最纯真的幻想?什么样的世界是真正的科幻,而什么样的世界才是现实?这一类问题不断困扰我们。
在回顾20世纪的科幻传统中,乌托邦、异托邦以及恶托邦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直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在这里我只用最简略的方式回顾从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中国的小说实践,既有国家的、历史的、人文的,也有伦理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在1907、1908 年的《黄金世界》和《新纪元》,或者陆士谔在1910年所作的《新中国》,这些作品都以最神妙的方法引导我们进入对未来乌托邦的想象。而为了这个乌托邦想象,我 们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寻觅,来定义,或再一次的推翻,再一次的建立。1903 年,当鲁迅翻译儒勒· 凡尔纳 (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的时候也提出了对乌托邦的想象“: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 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对于鲁迅来讲,当整个世界在变动的时候,他感叹的是“琼孙之福地 , 弥尔之乐园”, “遍觅尘球,竟成幻想”。而在世事纷扰的时候,“冥冥黄族, 可以兴矣”,这正是中国所谓黄种人的民族再一次证明可以崛起的契机。
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头,科幻已经不断给予我们许多想象。但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样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在文学的领域里逐渐消失了。我们在文学里所看到的关于广义的乌托邦叙事,其实是被恶托邦所取代。当沈从文写出《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写出《鬼土日记》,老舍写出《猫城记》,甚至在抗战时间张恨水写出 《八十一梦》的时候,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不再有可以艳羡的、可以期望的乌托邦的未来。相对于此,我们看到的是恶托邦。
就我个人研究所得,我认为所谓的乌托邦论述逐渐式微,当然是和当时写实主义的信条有关,也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发生紧密的连带互动。少数作者,如顾均正在1949 年写的《和平的梦》,有一点受乌托邦的影响。但真正的乌托邦论述事实上出现在政治领域。1913年康有为 《大同书》第一次以书面形式部分刊行,所投射的乌托邦愿景到今天仍然魅惑了许多读者。1925 年张竞生提出 《美的社会组织法》,以纯粹的审美和身体的重新再造,想象出一个最健康、最健美的社会,这是从身体出发的审美乌托邦。或者像毛泽东在1949年革命成功前夕,提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强调未来的中国民族如何发扬民主、如何安居乐业等等,无一不投射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分子以及政治领导者的寄托。但乌托邦想象很快融入充满政治化的预言以及文学操作里。而在1950~1960 年代,事实上有许多广义的所谓乌托邦或是科幻文学出现。如叶永烈1961年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到了1970 年代末期才得以第一次出版,成了新时期非常重要的畅销书,以及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有许多科幻乌托邦的场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重要的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曾经提出,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在1950~1960 年代,几乎成为一种所谓的为政治背书的文学(lobby literature),它和政治纲领或教条相互呼应,成为一种僵化的写作方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或许在一个全民充满了政治激情的时代,乌托邦写作的存在或者消失,提示乌托邦或更广义的科幻叙事建构,其实是我们政治潜意识的一部分。而如何看待以科幻出现的政治潜意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中,永远是一个值得挑战的话题。这是我个人对于所谓广义的科幻文类传统的回应。
2 “边缘”视野:科幻激发时代的另类想象力
我对于当代科幻作者写作的姿态或题材甚至风格有三种观点。首先,我认为是一个入门级的观点,即所谓历史政治的预言。我们总是在科幻小说里去找寻国家的预言,找寻历史的预言;从不可能的、匪夷所思的语境里,想象历史和国家的过去与未来。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虚构方式,科幻小说的魅力在此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到老舍《猫城记》;从旅美作家张系国《城》到刘慈欣《三体》,都有意无意投射国族文化寓言和预言。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科幻作者如何发挥认识论(episteme) 的能量。王晋康先生所一再强调的在科幻领域里,无论论述的可信度与否,你必须给出一个知识体系, 一套言之成理的说法。在一个看似荒诞不羁的情境里,展现出一个前所未闻的,但又自成一格的知识论新构造。这在刘慈欣《三体》这样的硬科幻作品里,尤其看得清楚。 构筑知识论之余,作家也操作情动力(affect)——就是喜怒哀乐的情绪,或者经过喜怒哀乐所媒介化、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文化制作和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情动力和知识论相互作用,塑造了我们对于中国国体或中国主体的想象。不论是刘慈欣的壮丽雄浑,韩松的诡异沉郁,台湾作家纪大伟、洪凌的“欲”想天开,当代科幻作家的理念铺陈、情感投射如此变化多端,不是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主流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是最让我们艳羡的部分。
再次,当代的科幻作家对于什么是“后人类”也做出 反思。“后人类”听起来好像不过是后学的流风余绪,事实上,它一方面当然有后学论述的根源,解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对于“人”的论述,但是这“后人类”并 不代表我们人类到此就告一段落了,而是在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人文观点,或者已经习以为常的想法之外,对人之 所以为人,人所创造的文明,人所能够形塑于生命情境的 各种可能再一次做出反思。而所谓“人”的观点,西方的文艺复兴以来已经过几次重大思考。当代中国作家也参与了后人类的反思。不论是宇宙的探险,星际大战的大灾难、大胜利,各种人工的智慧所产生的机器人,或者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另类塑造,一种新的“人”的观点逐 渐浮现,让我们重新思考。
这三个观点其实并没有轻重或先后之别。以下,我以这三个观点形成的复杂脉络来回顾我所敬重的科幻作家的作品。比如,香港作家董启章的《繁胜录》《梦华录》以南宋的《西湖繁胜录》和《东京梦华录》这样遗民写作来投射1997 年香港回归前后暧昧的情绪反应。他的《地图集》则重新塑造—虚构香港地理疆界。又如陈冠中先生,也是一位带有科幻意识的香港作家,他的《建丰二年》写 出了他所谓的“乌有史”,重新叩问历史,重新推演了另外一种时空的顺序。经过时空穿梭的旅行,我们习以为常 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点似乎在这里被打乱了。
在种种政治或历史的感叹之余,这些作家也同时在发问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写作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身体的能量,用什么样的深情来看待历史。张系国是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1980年代以来,他以三部曲来反思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的命运何去何从,写出一系列史诗般的小 说。就像陈思和教授所说,科幻曾经是台湾风云一时的文类。除此之外,科幻女作家洪凌几乎有与刘慈欣《三体》 般庞大的“太空歌剧”式的气魄,但是作品却雷声大雨点小,她的兴趣转而对身体,尤其是情欲所激发的能量和宇 宙交会所形成的奇观。同样,台湾作家纪大伟的《膜》从 当代同志世界的角度,对人工人、自然人之间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生理、伦理关系做出想象。这些科幻作品穿梭在不同的人类情感领域,询问身体的疆界在哪里,以及知识 体系之间的互动产生别样的效应。
另外,像骆以军——台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除了 《西夏旅馆》之外,在2014 年写出了作品《女儿》,向我们最亲近、最亲爱的女性对话:他的角色到底是不是人,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造人?看看我们周遭,我们所亲近悉的“人”的疆界在哪里?骆以军在这里贯注了千万柔情。他的抒情笔法是我在阅读大陆科幻作品的经验里还没有看到过的。在这个意义上,《女儿》是一部处理人工智慧和情动力之间张力的佳作。
当重点回到中国内地的时候,我们发现另外一种风景,再次说明不论是政治或历史的预言,不论是情动力或者是知识体系的再一次组合,还有对后人类文明的思考,内地三位重要科幻作家——王晋康、韩松、刘慈欣,还有年轻一辈的作者,都有可观成绩。王晋康的惊悚作品《蚁生》,刘慈欣的《三体》,等等,成为塑造21世纪现代中国经典的一个最重要的痕迹。
我们都知道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等。我们当然都尊敬他们的写作成就,但就21世纪第一个十年而言,谈大的突破,大的创造力, 我个人以为科幻作家的成绩超过主流作家。他们写出了让我大开眼界的作品。除了大家最为推崇的刘慈欣,还有供职于新华社的韩松,他白天报道人生的光明面,晚上书写人生的黑暗面,最近的苦恼是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他的《地铁》《2066 年之西行漫记》等作品把人类文明最黑暗的、最不可思议的面向导向深不可测的渊薮。而刘慈欣则完全面向宇宙星空的“终极爆炸”(套用王晋康作品名),这两种极端的辩证的拉锯,产生了当代中国小说和论述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
除了这些我们都熟悉的中国作家和作品之外,我还特别想提到香港作家董启章的《时间繁史》,他以50万字篇 幅讲述人工智慧如何应付香港的历史的僵局;以及台湾作 家吴明益的《复眼人》,讲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搏斗;或者像伊格言《零地形》讲述核子战争之后,在一切的人类文明毁灭之后,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话题都再次显示科幻小说的作家碰触了主流作品所未曾注意或不敢书写的话题。这种自愿站在边缘,甘居异端的能量和想象力,我以为是让中国当代文学,甚至广义的政治历史的想象力,得以前进、展开创造力的一种契机。
3 幽暗意识:科幻开启重新看未来世界的方法
我个人曾做过一项观察,即在过去,尤其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准的一个文学书写的传统,特别强调感时忧国,特别强调文学反映人生,甚至创造和改造人生。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所谓的忧患意识,常常是大家居之不疑的创作焦点。我无意否定忧患意识,这是现当代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写作态度。但是我在这里更要提出,相对于忧患意识,“幽暗意识”可能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们所给予我们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份礼物。沿用张灏教授的看法,幽暗意识不仅指的是各种理想或是理性的疆界以外的不可知或不可测的层面,同时也是我们探触和 想象人性和人性以外、以内最曲折隐秘的方法。想想在国 族论述之外,庞大的宇宙星空所展现出种种不可思议的能量,以及文明存亡的抉择,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性,幽暗意识不再被简单地规范为五四以后感时忧国的传统,它引领我们思考、反省一个更广大的、更深不可测的生命领域。
幽暗意识当然有论述的渊源,我想说的有三点。第一,科幻小说教给我们重新看世界的方法。或用宋明炜教授的话来讲,在似乎什么都看不见或看不到的时候,它又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在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第二,科幻作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梦的解析术”,教导我们如何入梦,也教导我们如何惊梦。第三,科幻作家用他们的作品营造了无数特别有趣的,各种各样奇怪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有的像密码,在读者的眼下自然就可以传递出一个庞大的,不同于你我一般所知道的知识。而这些密码用最简单的方式,往往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熟悉最近这些年科幻作品的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发射出去的密码,像是2044 代表什么,2047代表什么,2066 代表什么,或2185 代表什么 (指夏笳著《2044 年春节旧事》、韩松著《2066 年之西行漫记》、刘慈欣著《中国 2185》等以数字为名的科幻文学 作品——编者注)。这些密码形式的东西,让我们了解到在所谓的国家、民族、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最广袤的,最深不可测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想象力驰骋的境界,也是创造文明的一个契机。
而什么样的世界是我们愿意去驰骋的世界呢?或者什么样的世界是我们希望离开的世界呢?1907 年,碧荷馆主人在《黄金世界》中,想象着新中国一切最美好的时候。但我们不曾忘记鲁迅在《影的告别》里面所告诉我们 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的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我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于当代科幻小说的最深敬意,因为他们是一群自甘于站在各种各样疆界的边缘,做出自觉和自为选择的作者,是一群不只具有幽暗意识,更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想象力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