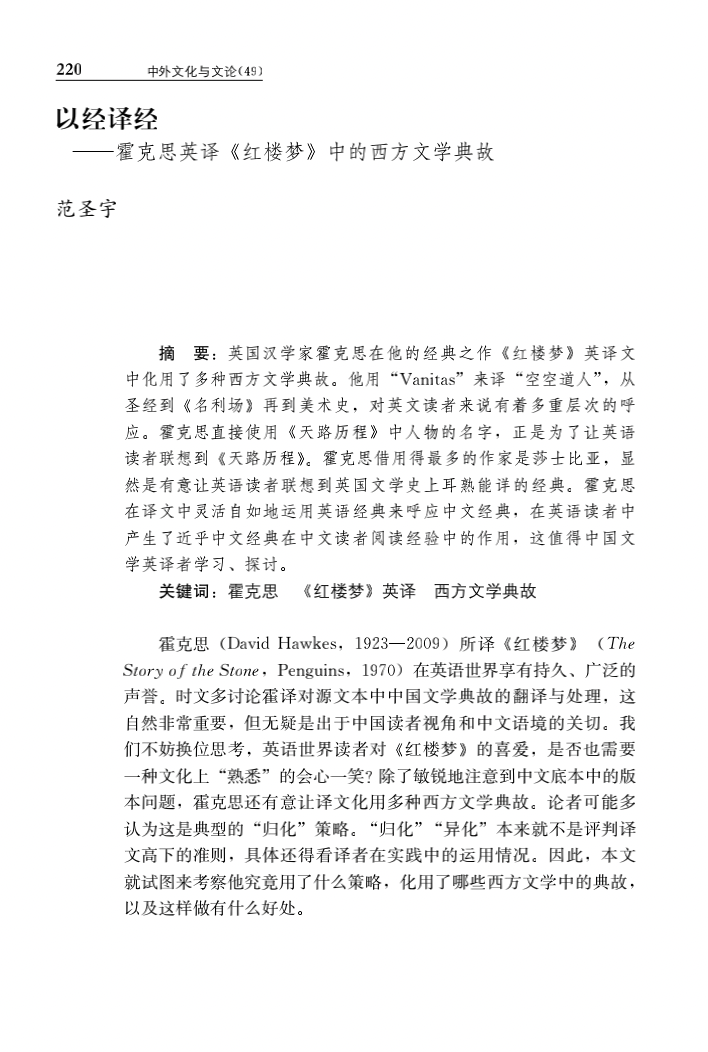
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所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Penguins,1973-1980)在英语世界享有持久、广泛的声誉。时文多讨论霍译对源文本中中国文学典故的翻译与处理,这自然非常重要,但无疑是出于中国读者视角和中文语境的关切。我们不妨换位思考,英语世界读者对《红楼梦》的喜爱,是否也需要一种文化上“熟悉”的会心一笑?除了敏锐地注意到中文底本中的版本问题,霍克思还有意让译文化用多种西方文学典故。论者可能多认为这是典型的“归化”策略。“归化”“异化”本来就不是评判译文高下的准则,具体还得看译者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因此,本文就试图来考察他究竟用了什么策略,化用了哪些西方文学中的典故,以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一、空空道人
我们先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中的人物名字时,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策略。男名译音,女名译义,主子丫头,僧俗女道,各各不同。第一回中出现的“空空道人”就是一个有趣例子。曹雪芹所谓“空空”,呼应的是儒释两家的经典,曹公却偏偏称为“道人”,这是大有深意的。《论语·子罕》中有:“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说的是儒家大圣人的谦逊。《大智度论·卷四十六》载:“何等为空空?一切法空,是空亦空,是名空空。”这说的是佛家一切皆空而又不执着于空名与空见。另外《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中有:“文殊师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无侍者?’维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又问:‘以何为空?’答曰:‘以空空。’又问:‘空何用空?’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又问:‘空可分别耶?’答曰:‘分别亦空。’又问:‘空当于何求?’答曰:‘当于六十二见中求。’又问:‘六十二见当于何求?’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而《梵网经》中则有:“若佛子,以悲空空无相。……空空照达空,名为通达一切法空。空空如如,相不可得。”我们暂且不必详细讨论“空空”一词在《红楼梦》中究竟何意,但其源自儒释两家经典是确凿无疑的。
霍克思把“空空”译作拉丁文“Vanitas”,典出基督教《圣经·传道书》,这与原文是恰如其分的经典对照。武加大译本(Vulgate)中作:“Vanitas vanitatum,dixit Ecclesiastes;vanitas vanitatum,et omnia vanitas.”而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s Version)译作:“Vanity of vanities,saith the Preacher,vanity of vanities;all is vanity.”(和合本译文: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读者不难看出“空”字在这句经文的中译文里重复了五次。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名利场》中就曾经借用过:“Vanitas vanitatum!Which of us is happy in this world?Which of us has his desires?Or,having it,is satisfied?”(杨必译文:“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这正是在呼应《红楼梦》“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喻。此外,“Vanitas”也是西方美术史上一种有名的静物象征画,或译作“虚空画”。虚空画试图通过描绘静物来表达在绝对的死亡面前,一切浮华的人生享乐都是虚无的。
这些作品中的物体往往象征着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以及死亡,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常常出现骷髅。这是在提醒受众光阴转瞬即逝,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红尘乐事并不能持久。《红楼梦》最深刻的主题之一,不正是如此吗?甲戌本第一回二仙师言:“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第十二回贾瑞在风月宝鉴的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骷髅。庚辰本双行夹批说:“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因此,霍克思用“Vanitas”来译“空空道人”,从圣经到《名利场》再到美术史,对英文读者来说有多层次的呼应关系,也十分贴切于《红楼梦》的主题。
二、《天路历程》
对《红楼梦》中众丫鬟的名字,曹雪芹显然是自出机杼,新雅不落俗套。第五回中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出场时,脂批曾言:“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与并肩。”对于这些人名,霍克思译得也很有特点。他把鸳鸯译作“Faithful”,平儿译作“Patience”,傻大姐译作“Simple”,善姐译作“Mercy”这几个名字放在一起,吴世昌先生的评价是:“令人觉得她们不是《红楼梦》里漂亮的少女,而是《天路历程》一类‘圣书’中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十几年前在拙著《红楼梦管窥》中,笔者也同意过吴世昌先生的看法。乍一看确实如此,这四个人物的名字都是直接从《天路历程》里摘出来的。然而,问题是霍克思难道不能有更好的方法,非要让他笔下的少女们跟《天路历程》中的人物取一样的名字不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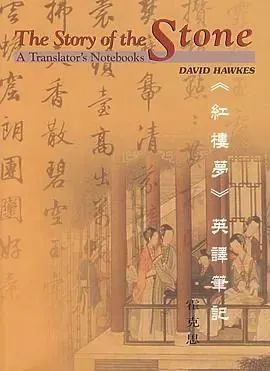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
这个问题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查阅《红楼梦英译笔记》可见,鸳鸯最早译作“Ducksie”,傻大姐最早译作“Daftie”,可见霍克思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这些译名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笔者目前的观点是:霍克思并非黔驴技穷,恰恰相反,他是有意为之,直接使用《天路历程》中人物的名字,正是为了让英语读者联想到《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是用英语写的第一本小说,也是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经典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被翻译成了200多种语言。牛津大学诗歌教授麦凯尔(J.W.Mackail)曾说:“班扬不只是位艺术家;《天路历程》不只是部艺术品。这部‘梦境寓言’呈现了一个探察到生命深层之人的清晰视野。”《红楼梦》不妨也可以被视为宝玉经历的一场“梦境寓言”,宝玉最终看破红尘,全书展现的也是他的成长经历,或者说是探索生命深层的过程。《天路历程》的第一卷完完全全就是写作者的一个梦。这个最广为人知的宗教寓言首版的封面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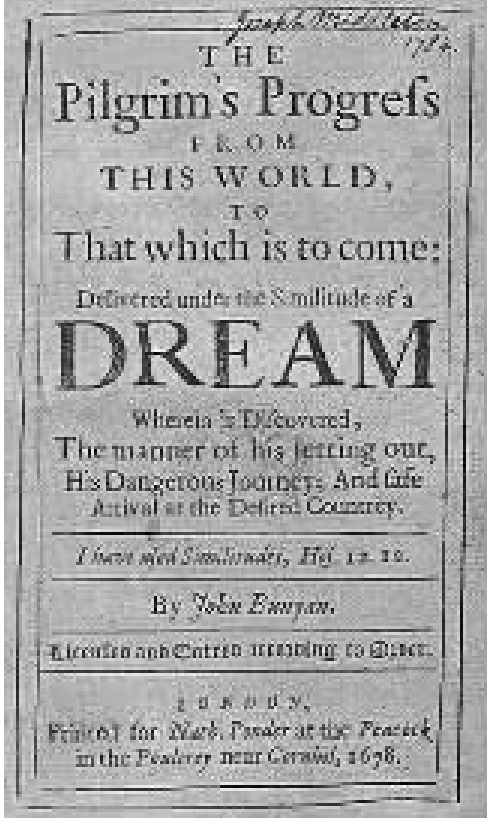
读者不难看出,其中“DREAM”这个词比我们熟知的“Pilgrim's Progress”更抢眼。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这一呼应关系。但如果单单是四个人物的名字借用了《天路历程》,那恐怕还不能说明什么,霍克思在人名、地名的双关寓意上,都在有意无意地呼应《天路历程》这部小说。更突出的例子如《红楼梦》第五回的“迷津”译作“Ford of Error”,与之对应的是《天路历程》中的“Hill of Error”。而“木居士”“灰侍者”译作“Numb and Dumb”,笔者认为也是受了《天路历程》中天国城附近的那条河上两位能渡河的以诺与以利亚(Enoch and Elijah)的启发。“betwixt the mand the Gate was a river, but there was no bridge to go over;[...] but there hath not any,save two,to wit,Enoch and Elijah,been permitted to tread that path.”(在他们和天门之间横着一条河;河上没有桥,河水很深……只是自创世以来,只允许过两人,就是以诺和以利亚踏上那条路。)霍克思不过是用两个押尾韵的名字取代了班扬笔下两个押头韵的名字,信仰得救的只能是少数,这在两部小说中的描写都是一样的。此外,《天路历程》与《红楼梦》还有另一层呼应关系。曹公曾借石头之口言:“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班扬在卷首题词也说:“愿这小小的书化作祝福一份,赠予那些喜爱这小书也喜爱我的人们……又愿它把一些迷途的人说服,让他们的脚步和心灵转归正路。”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显然十分接近,一是娱乐,二是劝善。文学的这两种作用如果要追溯到古罗马,那正是批评家们所谓的“dulce et utile”(sweet and useful)。
更直接的借用当然也有,比如第一回中,甄士隐所住姑苏城:“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此处“十里”隐“势利”,“仁清”隐“人情”,这是脂批明点过的。霍克思的译文作:“Out side the Chang-men Gate is a wide thorough-fare called Worldly Way; and somewhere off Worldly Way is an area called CarnalLane.”这里“Worldly Way”与“Carnal Lane”的译法很巧妙,不过他暗中借用的是《天路历程》中的一句:“The gentleman's name was Mr Worldly-Wiseman,he dwelt in the town of Carnal-Policy.”这两个地名的译法,显然也是从《天路历程》里借来的。霍克思显然是要英语读者联想到班扬,否则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天路历程》。不过总体来说霍克思对班扬的借用还不算太多,毕竟宗教文学经典与《红楼梦》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霍克思借用得最多的当数莎士比亚。译者显然也是有意让英语读者联想到英国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经典。
三、莎士比亚
《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湘云黛玉联句“三五中秋夕”,霍克思译作“Fifteenth Night of the Eighth,Mid-Autumn Moon”,这里呼应的是两部莎剧:《第十二夜》(The Twelfth Night)与《仲夏夜之梦》(A Mid Summer Night’s Dream)。第一回中的元宵佳节,霍克思译作“the Fifteenth Night”,也是在呼应“The Twelfth Night”。英文里本来没有“the Fifteenth Night”的说法,霍克思生造出一个词来译正月十五元宵节,目的在于提醒读者注意这是与“The Twlth Night”类似的一个节日。基督教圣诞假期中的最后一夜为“第十二夜”,也就是一月六日的主显节(Epiphany),据说莎翁这部戏首演也是在“第十二夜”。《红楼梦》第五回中写妙玉的曲子《世难容》,霍克思译作“All at Odds”,则是出自《李尔王》第一幕第三场,高纳里尔抱怨父亲:“他一天到晚欺侮我;每一点钟他都要借端寻事,把我们这儿吵得鸡犬不宁。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Every hour He flashes into one gross crime or other / That sets us all at odds. I'll not endure it.)妙玉跟李尔王当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两个人物都让周围的人觉得无法忍受这一点是相通的。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宝玉赞叹紫鹃:“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典出《西厢记》。霍克思的译文是:
If with you ramorous mistress I should wed,
’Tis you,sweet maid,must make our bridal bed.(I.626-627)
“sweet maid”和“bridal bed”出现在好几部莎剧中,特别是“bridal bed”(新床、婚床),看似喜庆,其实并不是什么好兆头。《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朱丽叶恳求母亲不要把她嫁给帕里斯:
啊,我的亲爱的母亲!不要丢弃我!把这门亲事延期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也好;或者要是您不答应我,那么请您把我的新床安放在提伯尔特长眠的幽暗的坟莹里吧!
O,sweet my mother,cast me not away
Delay this marriage for a month,a week;
Or,if you do not,make the bridal bed
In that dim monument where Tybal lies.
朱丽叶后来果然惨死在“提伯尔特长眠的幽暗的坟莹”里,原本喜庆的婚床,却成了她永远的安息之所。而满心欢喜马上要迎娶朱丽叶的帕里斯在朱丽的说:
这些鲜花替你铺盖新床;
惨啊,一朵娇红永委沙尘!
我要用沉痛的热泪淋浪,
和着香水浇溉你的芳坟;
夜夜到你墓前散花哀泣,
这一段相思啊永无消歇!
Sweet flower,with flowers thy bridal bed I strew,—
O woe!thy canopy is dust and stones;
Which with sweet water nightly I will dew,
Or,wanting that,with tears distill’d by moans:
The obsequies that I for thee will keep
Nightly shall be to strew thy grave and weep.
他用的也是“sweet”bridal bed”这两个词。它们显然都是褒义词,但用在这里真是莫大的反讽。字面的优雅美丽,更添哀悼悲伤的气氛,更深入地刻画了帕里斯的悲痛。
《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王后哀悼奥菲利亚时用的词也是这两个:
好花是应当散在美人身上的;永别了!(散花)我本来希望你做我的哈姆雷特的妻子;这些鲜花本来要铺在你的新床上,亲爱的女郎,谁想得到我要把它们散在你的坟上!
Sweets to the sweet!Farewell.
(Scatters flowers.)
I hop’d thou shouldst have been my Hamlet’s wife;
I thought thy bride-bed to have deck'd sweet maid
And not have strew’d thy grave.
从以上几个片段,读者不难体会到霍克思译文的精妙之处。他有意点染的是从字面上看不出来,却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悲剧色彩。“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这是张生对红娘说的话,宝玉借来对紫鹃说,是半真半假地对黛玉开玩笑。当然最后张生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而虽说脂批提到“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但宝黛后来并非如此,“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一个早夭,一个出家,他们并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因此,霍克思用“sweet maid”和“bridal bed”这两个看似褒义、实则暗讽的词,实际上已经在用莎士比亚的经典名作呼应,并暗示英文读者宝黛的悲剧结局。这种构思是十分精妙的。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其实霍克思这个手法也是从曹雪芹那里借来的。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薛宝钗的金锁上面的铭文分别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乍一看也是“吉利话儿”,“仙寿恒昌”“芳龄永继”寄托了贾府和薛家对两位继承人的极髙期望和美好祝愿,但曹公十分狡猾地在前面加了“莫失莫忘”“不离不弃”这两个条件句,使得“金玉良缘”最后还是成了一场空。它们虽为“吉谶”,可是寄托了贾家希望的宝玉最终还是被“失”并且“忘”了,而宝钗也因为宝玉出家而被“离”被“弃”。庚辰本夹批云:“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人物的悲剧命运是通过字面的点染暗中透露给读者的。霍克思借用莎士比亚似褒实贬的译法,可以说真正学到并且灵活运用了曹雪芹的写作精髓。
四、其他
除了莎士比亚,霍克思化用英语经典的地方俯拾皆是。有时他借用的是英语译作中的经典,比如将第四回中《列女传》译作Lives of Noble Women,显然是在呼应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英译者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第二十八回中的锦香院,霍克思译作“Budding Grove”,呼应的是普鲁斯特的名作《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hrche du temps perdu),C. K. Scott Moncrieff的经典译作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的第二卷题名正是Within a Budding Grove。
霍克思译作中还有化用英语诗歌的成分,比如《红梦楼》第二十七回中宝钗扑蝶的一段:
想毕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
Her mind made up she turned round and began to retrace her steps,intending to go back to the other girls;but just at that moment she noticed two enormous turquoise-coloured butterflies a little way ahead of her,each as large as a child’s fan,fluttering and dancing on the breeze.((II.4-5)
这里最后一句“fluttering and dancing on the breeze”,借用的是华兹华斯的名作:“我好似一朵孤独的流云。”(I wander lonely as a cloud)第一节的最后一句,霍克思只改了一个介词: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host,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霍克思译文中灵活运用英语文学经典的部分,当然远不止这些。笔者相信更高明、更熟悉西方文学经典的读者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阅读这样的译文,是一个不断有惊喜的过程。正如笔者在“校勘说明”中说过的:“用心的读者无疑可以从中找到许多有趣的地方,勤勉的博士生或红学家也一定能发现更多译者创造性的修改。”当然,前提是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和较好的西方文学经典修养,否则未必能看得出霍克思有意呼应的典故。这正暗合了《红楼梦》的结尾所说:“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
五、结论:以经译经
笔者认为霍克思的方法是以经译经——以英文经典译汉语经典,这是真正做到了中西结合、融会贯通。评论家们常说汉译英有三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准确、流畅、地道,首先是语法正确、语义准确,然后是清楚明白、流畅可读,最后是近乎母语的地道表达。霍克思的译文让笔者觉得,真正的高手在这三个层次之上还有另一个层次,那就是以经译经的融会贯通,也就是说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英语经典来呼应中文经典,在英语读者中也能够起到近乎中文经典在中文读者的阅读经验中的作用。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冯象曾说:“译文不必不如原文,尤其是文学经典。因译本的真生命不在模仿、再现,而是创造;是与原著对话、相持,以汲取其力能,传布新的思想,探求新的意境,自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他的重点不是说译文不必不如原文,而是在于译文与原著之间的对话,也就是在以经译经这一层次上的呼应。
相对来说,中文译者能做到前三个层次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这最后一个层次,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文学英译应当企及的高度。因为译作只有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经验中起到心有灵犀、息息相通的作用时,才能说是真正走出去,真正起到了在两种文化与两批读者之间架桥铺路的作用。这就是钱锺书所说的“化境”,当然,这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必须对两种语言及文化中的经典都极其熟悉。正如陈德鸿所言:“读者对于这两种系统的熟悉程度必然会决定其是否能够对译文进行可靠的或更加准确的诠释。”而同样的道理,在此之前,译者对于这两种系统的熟悉程度也必然决定其是否能够对原文进行可靠的或更加准确的翻译。
库尔提乌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这部巨著中说过: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当下”(zeitlose Gegenwart,timeless present)。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因此,维吉尔中有荷马,但丁中有维吉尔,莎士比亚中有普鲁塔克和塞内加,歌德的《格茨·冯。贝利欣根》中有莎士比亚,拉辛与歌德的《伊非格涅》中有欧里庇得斯。我们时代的文学同样如此:霍夫曼斯塔尔中有《一千零一夜》和卡尔德隆,乔伊斯中有《奥德赛》,艾略特中有埃斯库罗斯、佩特罗尼乌斯、但丁、特里斯坦·柯比埃尔以及西班牙神秘主义。这些相互交织的关系乃是我们取之不竭的财富。
库尔提乌斯所谈的是欧洲文学这个整体,其中当然也包括语际书写与翻译,正如杨乃乔所说:“两种异质语言在语际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又是必须的,所以语际翻译永远是创造性书写——creative writing。”库氏所谈还是在欧洲语言系统内的情形,霍氏译文则跨越了英文与中文经典两个并不同根互生的传统。霍克思的用意显然是要化用西方文学经典来创造一部用英文重新书写的中国经典《红楼梦》,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以经译经”。
但是,霍氏为什么要用这些典故呢?显然他的互文效果针对的是英语世界的读者阅读感受与审美体验。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曾说他在读霍氏译本的时候不时微笑,毫无疑问是因为联想起自己的阅读经验。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接受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也就是埃文·佐哈(Evan Zohar)所说的,中国文学还在英语世界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所以他选择依赖中心文学——英语文学经典来抬升自己译文的文学地位。霍克思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他让英译本《红楼梦》不仅成为学者的案头读物,更是成为带来审美愉悦的一个艺术文本。阐释学中所谓的“期待视野”促使作为英国学者的霍克思坚信,中国文人的游戏笔墨《红楼梦》,就应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发现处处皆典,可以让有心的读者会心一笑,既流畅轻松又令人拍案叫绝。
范圣宇,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2019年度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此文即范博士在中心访问期间展开的持续研究的成果。著有《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英文专著 The Translator’s Mirror for the Romantic: Cao Xueqin’s Dream and David Hawkes’ Stone 即将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曾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汉英对照霍克思、闵福德译五卷本《红楼梦》版本校勘。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汉英互译,中国古代文学。
转载自公众号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