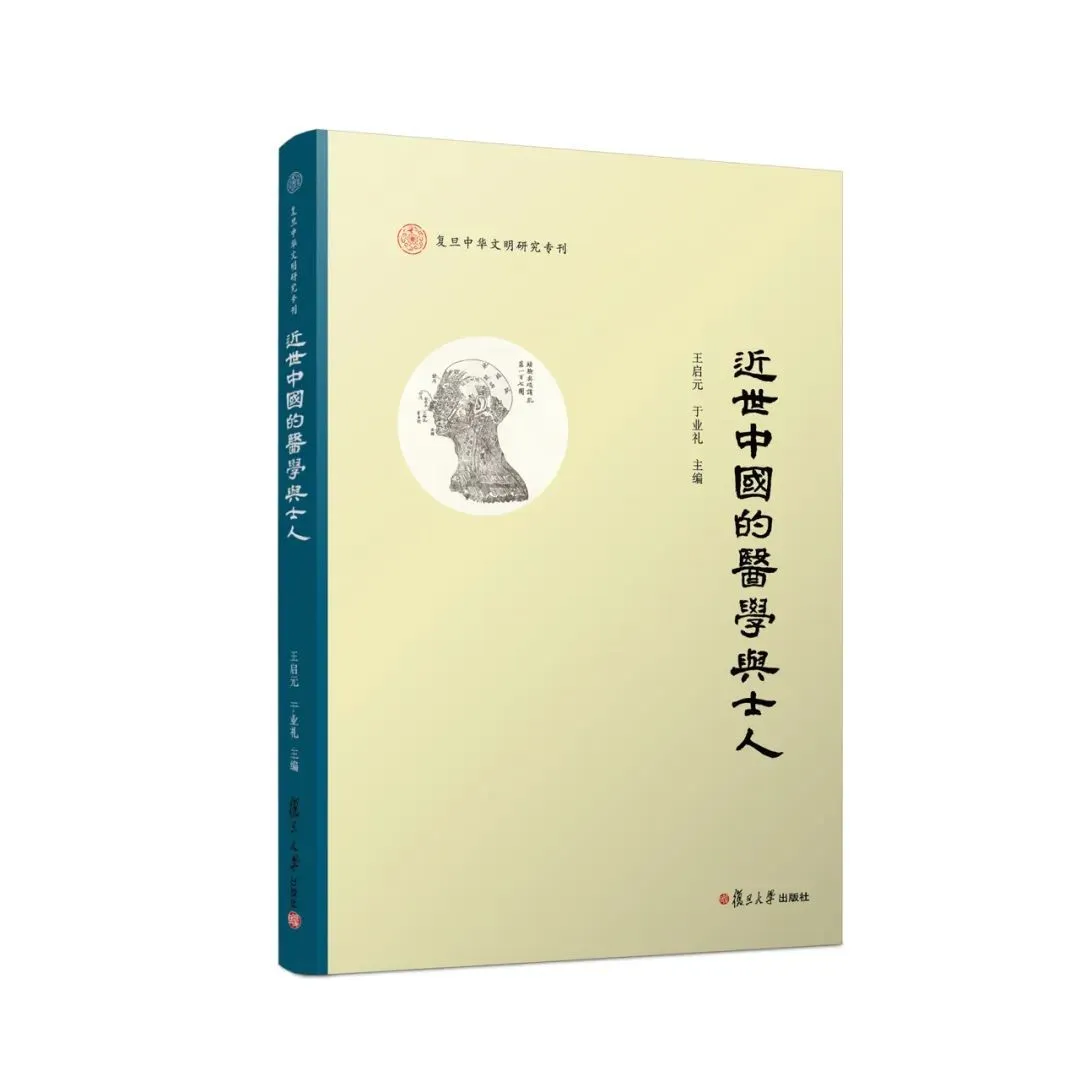
《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
王启元、于业礼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本次论文集结集机缘,得自2023年夏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同名工作坊“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感谢前来赴会的各地文史、医药界同仁,同时致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对论文集出版的支持。去年举办此次工作坊时,正值疫氛甫靖,云霾初霁,海内同好终于从云端线上下降尘世,当面执手,坐而论道。此去经年,医学人文话题亦已渐成显学,学人竞相预流。我辈后学,当克励驽庸,勉效绵薄,因有是小集问世,敬呈医学人文同仁几前。
绪论:彷徨于士人与医学之间 ——一种医学观念史的视角
医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学科,从古到今都是精英知识分子至为关注的话题。尤其是频繁地面对生老病死及大规模的传染病,前人出于个人及社群基本的生命自保,掌握医学救助与看护知识,成为精英知识分子与大部分普通人的“标配”,唯有知识的量级及观念立场的差异而已。近世以来,人们医学知识的更新,超过了史上任何时代;早期医学知识中诸多的内容,都受到新式知识、观念的挑战。西医的入华及现代医学训练的专门化,更是催生出新式的职业医生群体与现代医院制度,更使得近世以来人们的医学观念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望明清近世直至今日的医学观念接受,今天人们对于医生护士及医院认可与依赖的态度,放在五百年前估计并非如此。这其中的转变不仅受到中西医学文化交流的影响,也有来自本土医学观念和知识普及的影响。其中,本土医学的现代化中,除了可见的诊疗、护理、机构及知识的更新换代外,同时也伴随着本土整体医学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念史的变迁,是医学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医学话题,不仅有技术科学现代化的面向,同样也存在观念认识迭代的维度。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医学的态度,是观念史中值得琢磨的话题。首先,作为知识的医学,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排斥,虽然他们的首要任务无疑是制艺科考,但有不少人谙熟佛道及医学等书。一些看似与医学不甚相关的士大夫,仔细梳理之下,都能找出与医学间的一些联系。如理学大家朱熹,因与医人相交,碍于朋情,写过《送夏医序》《跋郭长阳医书》等序跋著作。其对医学知识的稔熟亦不在话下,如曾说过“陶隐居注《本草》不识那物,后说得差背底多,缘他是个南人,那时南北隔绝,他不识北方物事,他居建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八)这样的话,对如今研究《本草经集注》及陶弘景医学的学者都颇有启发作用。至于不少士人在医学上有所深研,或有所著述,更是和医学产生了密切关系。
熟悉医学知识,不代表他们认可医人身份。清代的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等),在医学史上更是号为“温病四大家”之一,曾写过《湿热病篇》这样的名著。同时他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氏著《一瓢诗话》,论诗不仅与乃师叶燮相合,还与名家沈德潜多有接近之处。但是,没有功名的他,在乃孙薛寿鱼所撰墓志铭中,竟“无一字及医”。据刘庆宇先生《薛寿鱼“无一字及医”原因探析》考察,薛雪生前便不愿以医示人,“公卿延之不肯往”。其孙薛寿鱼不提及他医生的身份,可能是出于“为先人讳”的目的。薛寿鱼将墓志铭寄与薛雪生前的好友袁枚,袁枚对薛寿鱼这一做法十分不满,主要原因是不忍好友薛雪在医学上的建树被埋没。袁枚也在愤怒之下,写下《与薛寿鱼书》这一不朽名篇。向薛寿鱼质问说:“仆昔疾病,性命危笃,尔时虽十周、程、张、朱何益?”不过由薛寿鱼和袁枚的不同观点也可知,不同人出于不同目的,在判定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时,会得出不同结论。薛雪其人,今之文学研究者称其为诗人、文学家,医学研究者称其为名医,不过是所取不同罢了,不必过于苛求。
明代中期以后出版开始普及,医学知识也随之大量传播,科场的士子们不少也开始选择亲近医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观念,开始挑战之前歧视医人、名列“三教九流”的陋习。不过终其近世,对职业医人们的成见始终没有消弭过。陆家嘴的主人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南直隶上海县人)跋一篇书法作品时说,学书法要了解“点画波磔”的技巧,就如同学医需要掌握“望闻问切”一样的。之后其话锋一转道:“谚云,学书止于废纸,学医将至于废人。”这句话本身大意书法的尽头就是不再“废纸”(浪费纸),而学医的尽头竟是“废人”,既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医人。言下学书法还高过学医一筹。这无疑是明代人对医学的极端偏见。
著名戏曲家李渔(1611—1680,字笠鸿,号笠翁)祖上是中医世家出身,本人也粗通医药,正是这样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不少对医学从业者的揶揄与挖苦。氏著拟话本《连城璧》未集里有个医家马麟如的故事。麟如因为医术高明,每天赔了工夫看病,把自家的举业反荒疏了。“写惯了药方,笔下带些黄连、苦参之气,宗师阅卷看了,不觉瞑眩起来,竟把他放在末等”,因为天天看病抄方,竟然连科考都不会了,所以小说里说他:
别的还博而不精,只有岐黄一道,极肯专业致志。古语云:“秀才行医,如菜作齑。”
“齑”字本是指腌制过的韭菜,也泛指经腌制、切碎制成的菜。“如菜作齑”自然是作贱的一种说法,来指代身为秀才而行医的举动。很显然,在明清士人的观念里,行医者地位极低。相似的表述还见于清代中叶的名医陈念祖所著《医学从众录》,陈氏在自序里引了李渔小说里的两句俗话:
“不为宰相便为医”,贵之之说也。“秀士学医,如菜作齑”,贱之之说也。
这就是观念冲突时,普通医生遇到的自我认同困境。虽然都知道行医需要饱读典籍,还要有胆识有眼界,但明清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的观念根深蒂固,无法求取功名的读书人本身就低人一等,加上历来对行医者的歧视,让这种情势难以改变。笠翁《连城璧》亥集《贞女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有一个知县包继元巧用阴司城隍断案的故事。讲一个叫马镳的秀才,因为老朋友酒后戏言,就要休了妻。那位放厥词的老友姜某喝完酒马上得了所谓的“阴症病”过世,又死无对证。这位包大人在审姜某之死时,断的是庸医所致。小说里知县说道:
姜生员的供状,开口就说庸医害命,后面又说行将索命,他少不得就来相招了,何须本县惩治他?况且这样的医生,满城都是,那里逐得许多?自古道:“学医人废。”就是卢医、扁鹊,开手用药之时,少不得也要医死几个,然后试得手段出来。从古及今,没有医不死人的国手。
“学医人废”这句大俗话,同样颇为刻薄,指摘再大牌的医生医死几个人都是常事。行文至此,也可见李渔对世上贬斥医家之风,是了然于胸的。虽然熟悉传统医学,但李渔肯定不甚认可医学身份,只作为他小说戏曲的负面素材出现。
那些谑医的素材,除了有作者亲身经历,很可能也源自长久以来对庸医误人故事的流传与提炼而来。钱锺书先生曾引冯梦龙(1574—1646)《广笑府》中调侃庸医医死人,被逼抬棺出殡的故事:
一庸医不依本方,误用药饵,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责令医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殡,庸医唱曰:“祖公三代做太医,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连累妻,呵呵咳!”幼子曰:“无奈亡灵十分重,呵呵咳!”长子曰:“以后只拣瘦的医,呵呵咳!”
清人编《缀白裘》中也有相似情节。而这种谑医的情节,古今中外还颇有雷同;钱引法国的勒帅治(Le Sage)《跛足魔鬼》(Le Diableboiteux)中一对行医的兄弟,梦到颁布法令“凡医生未将病人治愈,不得索取诊费。弟梦官厅颁布法令,凡病人死于医手者,其出殡下葬时,该医须着服戴孝,尽哀往送”,其情同于《广笑府》《缀白裘》。此类情节虽然不同源,但其最初由调侃庸医而致讽刺整个医学界的基调是颇为相似的。这不仅是明清小说的独有的状况,应该是前现代时期传统医生群体普遍面对的问题。
就像曾经背负“离经叛道”骂名的摇滚乐,一直以来皆能得到年轻人的拥趸,背负“学医人废”骂名的医学典籍,其实也从来不乏来自精英士大夫阶层的读者。从秦汉以至明清,夸一位士大夫学识渊博,一般都会提到他天文地理、阴阳医卜“无所不窥”,显然医学知识是对大部分士人所认可的“渊博”之学。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留下了医学阅读的痕迹,但依然能找出不少爱读医书的士大夫群体,以证医学知识是古代士人中最重要的公共知识之一。
首先,对于普通儒生来说,知医可以是“孝悌”的重要鉴证。这一点前人探讨已多,林殷、陈可冀先生编《儒家文化与中医学》及论述儒医的著作,如陈元朋先生《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及薛芳芸先生《宋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等都有较多论述。前人论述中,认为将儒家孝悌思想和医学联系起来,主要是在宋代完成的。尤其以程颐、程颢为代表。两人都多次提出“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等说,经过总结,最终归结为“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也扩大开来,因家及国,便又有“为人臣者不可不知医”的说法。不过此观念或可上追至唐代或更早,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自序》中就有“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等语,此语或是上承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而来。另外,王焘《外台秘要·自序》也有语云“夫为人臣,为人子,自家刑国,由近兼远,何谈之容易哉”,又云“呜呼,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等。
其次,所谓“久病成良医”,病人中也多有爱读医书者。《汉书·汲黯传》载汉武帝欲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以多病不能胜任求免,汉武帝不准,让他以淮阳军民为重,可“卧而治之”。后世诗文中由此引申出“淮阳多病”“淮阳病”等典故,以自况多病。在历史上,士人务于读书而俭于健身,确实也容易生病。如书法家王羲之,身体就很不好。今人检视他所留下的书帖,其内容中涉及的疾病约有二十余种。生病求医,能得良医诊视自是幸事,但更多时候是“苦无良医”。这种情况下,很多士人便自读医书,学医以自救。甚至有不少名医都是由此而来。
第三,“卫生君子”爱读医书。医书中,常见“卫生君子”的说法;“卫”指保卫,“生”是生命,“卫生君子”乃是概言擅养生者。养生的目的无非是求无疾,或求长生。出于需要,自然最喜读医书。又由于擅养生者,多是道家者流,故此类人中,以道家或道教相关人物最多。早在《伤寒论·张仲景序》中,对于医学的作用,张仲景就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说法,后人读医书的目的,大多不出此范围。从以上所举三端即可知。当然也有不在上举三端之内者,如有人天生爱好医学,虽事儒业,而终归于医。还有如清代乾嘉诸老,崇尚汉学,以《素问》《灵枢》等医书为汉代之书,所以读之;且读而有得,并著有校释、笺疏等著作,则有大儒俞樾之作《内经平议》。
阅读之外,医学典籍的整理与出版更是离不开精英士大夫的参与。中古以前存世的医书不多,重要作者如葛洪、陶弘景等都带有鲜明的道教背景,医学行为可能与追求长生术、指导服食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时期,官修医书大量问世,如隋编《四海类聚方》,唐修《太素》《明堂经》《本草》,编《广济方》《广利方》等,其中虽都有职业医人的参与,但也有大量官员和儒生参与。唐政府编修医书之功,目前学界讨论得不多。总体来看,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医学教育编修教材,一是编撰实用的医方书。政府编撰医书的目的是为拯救民生,同时也是对神农、黄帝等圣皇事业的效仿,这两者都与儒家思想深切符合。至宋代,儒学昌盛,政府更是大力为之。宋代政府不仅多次组织编撰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无不在医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还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伤寒论》等医书十一部,使这些书成为定本,流传至今。孟永亮先生在《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中考察校正医书局的组成人员,除韩琦、范镇、钱象先三位提举外,还有校正医书官九人。十二人中,只有秦宗古、朱有章两位是翰林医官,其余皆为馆阁官员和知医儒臣。孟先生考察后,认为馆阁官员“但从校书所出具的注文来看,他们的医学知识丰富,医理水平也较高”。政府行为会成为一种新的模范,引起各官员和儒臣效仿。宋代官员和儒臣编医方书最多,此亦是一方面原因。
自《孟子·尽心下》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始,“兼济天下”便成为读书人的理想。医学“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也“可以利天下与来世”,编撰医书与士人“兼济天下”的思想最为符合。若不论政府行为的影响,宋代士人编撰医书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如许叔微编《普济本事方》,于《自序》中云:“余既以救物为心,予而不求其报,则是方也,焉得不与众共之。”陈造序《百一选方》云:“士君子以仁存心,凡其济世利人不能行,慊如也。”说得更为清楚明白。而这种通过编医书以“兼济天下”的行为,到明清时,更是大为昌盛,渐成风气。如蔡曰兰跋《痘科玉函集》云:“竹溪丁先生幼习举子业,卓有致君泽民大志,历数科而名不流,慨然托医道以利物。”将“医道”与“利物”对等起来。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眼里,医学已经是一种利世之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参与医书编撰的程度便更高了。与编撰医书一样,刊印医书也可起到利世的目的。如海宁蒋光焴刻徐大椿《洄溪医案》及《徐批外科正宗》两书,名医王孟英及时人许辛木等先生在写给蒋光焴的信中,最多称赞的便是其利世之功。
不管是出于何目的,无数事实都可证明,明清以后,士人在医学中的参与度是已经十分高了。尤其是在医书的编撰与印行中,都可经常见到士人的身影。而且在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士人对医学的重要性,如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自序》谓:“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便是从反面看到儒者对于振兴医学的作用。
士人对于医书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学的学术水平。尤其是清儒对《素问》《灵枢》等医书的校勘注释,对于后人理解古代医书十分有帮助。“医者读其书更触类引申之,将数千年之古学愈阐愈显,不且为抱残守缺者之幸甚耶”(俞鉴泉《俞曲园内经辨言序》)。不过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医学研究的门槛。如今日欲再行《素问》《灵枢》校勘研究者,不先在清儒基础上做一番工夫者,皆不敢下笔。
中晚清时,由于顾观光、孙星衍、黄丕烈等人的参与,医书的校勘出版,也远远超出前代。一是数量多,二是后出转精,校勘质量愈来愈高。如浙江书局设立后,接受曲园先生建议,于拟刻的《二十二子》中收入《黄帝内经》(含《素问》《灵枢》两书),于光绪三年(1877)刊印,成为《黄帝内经》重要的版本之一,也是清末民国医学界最常用的版本。此书以顾从德本为底本,由余肇均和黄以周任总校,冯一梅、孙瑛等人任分校,其中尤以冯一梅出力为多。冯一梅是俞樾门下高足,邃于古籍校勘,于近世传统医学研究贡献良多。虽然明清以来卓越的精英士大夫并未彻底改变世人对医者观念的转变,但依然对传统医学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医学事业与知识精英充分结合,也在未来从根本上改变世人对于医学的观感带去了契机。
在中国古代,职业医生是位为三教九流之一的贱业,曾遭到士人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面,医学又成为儒家思想中要求士人所掌握的基本知识。技术性的医生与医学知识被分离开来,成为一对矛盾体。而对容易生病的知识分子来说,技术性的医生又是他们最不可离开的一群人。如曾国藩,他在家书中多次告诫家人“病不延医”,而细观曾国藩书信和日记便可知,他身边其实围绕着一大批医生,来往极为密切。再如大儒俞曲园,也是一边骂着“吴地无良医”,一边稍有不适即延数医为之视。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知识分子便把矛盾点集中于医生身上,批判医生不读医书成为新的“风尚”。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医生群体,《医医》《医医医》一类的著作应时而出。如名医徐大椿也说“其害总由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医学源流论·医学渊源论》)。不过徐大椿到底是名医,同时也看到问题的其他方面,指出士人对医生的批判导致人们对医生不信任,而士人涉猎医书者能治小病而不能治大病,同样也为祸不小:
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医学源流论·涉猎医书误人论》)
但也只有徐大椿这一类医生中的精英能看到问题所在,普通的医生更多是借士人对医学知识的重视,而纷纷攀附。士人也欲借医学以达到他们“兼济天下”的目的,“不为宰相便为医”也因此成为医生和士人共同的幻想。
近世士人放弃“不为宰相便为医”的幻想,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考由此废止。科考晋升的破灭,解放了大多数的士人,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全新的社会形态之中,诸如进学堂、留洋、办报、工厂等“洋务”,成为当时新式读书人的首选。其中也包括对现代医学迸发兴趣的士人。
西方传入的医学诊疗知识,早在废除科举前已经在全国大范围传播,尤其开埠较早的南方诸省,在开埠前后便有大量西洋来华医生开始行医施药。西式的医馆药局纷纷出现,大量的新式医书也出版、流通,彻底改变了旧有医学知识的格局,深深地影响到中国本土的病人及诸多有识之士。这其中有逐渐认识到西式医学功效的病人与家属,同时也有热衷学习的本土士人。苏精先生《西医来华十记》中便有三章是专门介绍华人医生和学徒,其中有到爱丁堡求学的黄宽、在上海仁济医院担任学徒的黄春甫、协助合信(Benjamin Hobson)翻译《全体新论》的陈亚本、替伦敦会开拓北京和天津医学传教事业的满人学徒白瑜、任协和医学堂教习的李绍祖,以及一些由学徒出身的早期西医群体。虽然作者认为这批医人几乎被老师们如合信、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和德贞(John Dudgeon)的光环完全遮蔽,但仍是西医学在华传播不可或缺的人物。高晞教授也指出,在西医知识在华传播的研究中,异质文化的“本土化”特质是目前研究者比较热衷讨论的话题,但忽略了第一代西医受业者在这场跨文化传播中的贡献;这批西医学徒正是西医在地化的结果,也是近代医学观念转型的推动者。
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医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全新的机缘也应运而生,中医和西医也开启了接触与融合之路。最初,在“全盘西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学被认为是落后的、守旧的医学,或者是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时期,落后于西方医学所在的第四时期(周作人《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甚至一度要“取缔中医”。在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的努力抗争之下,才得以保存。之后,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开始自救,一方面提出“中医改良”“中医科学化”等,试图用西方医学理论的框架来改造中医。如从生理学、病理学分类角度重新为《黄帝内经》《难经》等书划分章节等,如杨则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教学时所编《内经讲义》(1925),分上中下三篇,下篇就包括“《内经》之卫生论”“《内经》之体质论”“《内经》之病理论”“《内经》之治疗理论”四节。秦伯未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地讲授《黄帝内经》,其讲义由学生陈中权、章鹤年编成《秦氏内经学》(1934)一书,也是分为《内经》生理学、《内经》解剖学、《内经》诊断学、《内经》治疗学、《内经》方剂学、《内经》病理学和《内经》杂病学等七章。可窥当时学人之观念。同时,唐容川、曹颖甫、张锡纯等人则提出“中西医汇通”学说,从临床实用角度出发,试图融合中西医。如张锡纯创制石膏阿司匹林汤,以清热解表,治疗浑身壮热的发热性疾病。时至今日,这一学说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借助现代医学之诊察手段,寻找优势病种,按病用药,也成为中医临床医生的普遍观念。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有专门研究可参。
近代以来,学医不仅可以治病救人,医学也成为救国的重要口号与实践,鲁迅先生远赴东瀛求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当然,更多留洋学医的青年士子,都选择用现代医学报效国家;现代医学为当时重要先进知识的代表,也已成相当共识。圣约翰书院创始人颜永京因为二子药物成瘾、三子患脑膜炎相继去世,而二弟如松不仅早逝还留下了多位侄子由其抚养,他迫切希望第二代能出一位医生,其子惠庆、德庆留美时都没学医,而由其亡弟如松子福庆完成遗愿,不仅成为耶鲁医学院第一位亚裔博士,还是近代中国医学教育的重要领袖。颜福庆早年回国在湖南长沙开办新式医馆与新式学堂,仍是西式医学尚未为人接受的时代,并伴有强烈的地方排外气氛,颜福庆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智慧,让湖南本地士人逐渐接受了新式医学。比如,因深谙病理生理学中大叶性肺炎的发病周期,颜福庆不费吹灰之力治好了湘中大佬谭延闿的高烧,这让其赢得谭氏及湖湘士大夫的信任,在长沙声名鹊起,也让湖南一带开始接受西洋归国的医人与新诞生的雅礼医院。相似的近代医学观念演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成为主流,职业医生逐渐也拥有了重要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甚至到颜福庆创办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推崇公医制,反复叮嘱医学学子为人群服务,不要去挂牌开私人诊所(《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这也反过来证明医学在精英士人观念中的地位之隆。
近世士人知识分子之于医学知识与职业间的彷徨与取舍,可以看作新旧之际中国医学观念史的缩影,其中医学史相关知识、观念、思想等多方维度,仍有着不少值得深思的话题。今天对于现代医学的信任与追求,在历史上可能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期间的医学观念现代化的历程,正好也与整个社会史、文明史的现代化相吻合。以往视角往往把医学现代化,看作整个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表征;若从医学观念史的角度看,那么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就是从巫术、教团、疾病、蒙昧、偏见之中,切近理性科学的医学观念与实践的过程;这一文明历程若有最终理想,应该就是人类的身心健康。
本次论文集结集机缘,得自2023年夏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同名工作坊“近世中国的医学与士人”。感谢前来赴会的各地文史、医药界同仁,同时致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对论文集出版的支持。去年举办此次工作坊时,正值疫氛甫靖,云霾初霁,海内同好终于从云端线上下降尘世,当面执手,坐而论道。此去经年,医学人文话题亦已渐成显学,学人竞相预流。我辈后学,当克励驽庸,勉效绵薄,因有是小集问世,敬呈医学人文同仁几前。
目录
交流与互鉴
张如青:清儒研治《内经》及其对中日医界的影响
杨东方:罗振玉首次赴日回流医书考述
成高雅:从《扁鹊仓公传汇考》看医学考证学派的学术与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关联
伦理与人文
潘大为: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
尹洁:医学哲学视角下的医学人文
医学的知识史
张苇航:医药擅能绘红妆——中国传统化妆与医药关系琐谈
王大伟:业儒、出家、行医——明末清初医家喻昌的人生与佛教
于业礼:冯一梅校勘医书事迹钩沉
李铁华:陈其昌居士生平及其医事活动考述
徐双:《军门秘传》略论
名医事迹
叶思钰:明代名医缪希雍年谱简编
近代医学机构与人物
任轶:近代法国医学教育在中国的实践——以震旦大学医学院为例
钱益民、唐一飞:医学教育的本土实践——颜福庆创办上医研究三题
陆明:颜福庆与中国医学团体发展
王启元:档案里的大历史与普通人——一位白衣天使的成长
陈渝生: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中的孙怀典
裘陈江:“输入泰西医学之一大关键”——赵元益及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