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晏然、褚國鋒:〈評Richard G. Wang, 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漢學研究》2024年第1期(第42卷第1期),第281-287頁。作者授權發佈。
書 評*
賀晏然 褚國鋒**
Richard G. Wang 王崗
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400 pages.
ISBN 9780674270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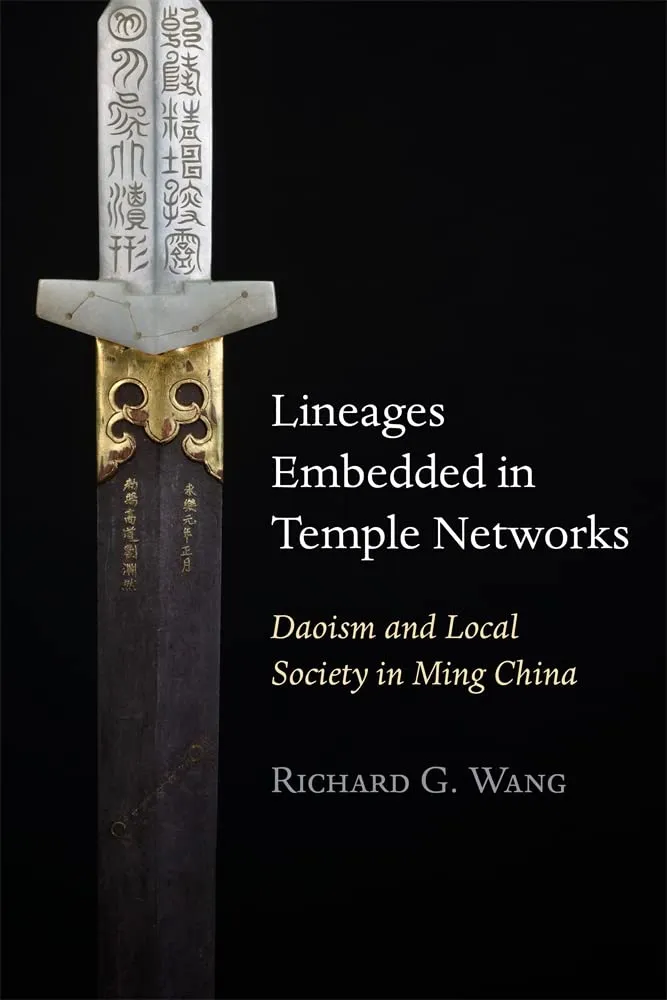
道教道派研究是建立道教史敘事、刻畫道教與傳統中國社會互動關係的途徑之一。道派牽涉道法、世系、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議題,是一個肩負「多重任務」的領域。受益于明清道教碑刻、志書、經卷等資料的陸續公開,深描明清道派發展的地方敘事逐漸形成一種趨勢。換言之,如何通過地方視角在長時段下處理制度與實踐、中央與地方、內地與邊疆等因素影響下的道派發展差異,同時重思明清道教的基礎結構、發展特征和社會功能,並與明清史研究形成深層次的對話,正成為學術界的致力方向。
繼《明代藩王與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護教》之後,王崗研究明代道教的新著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試譯為:《嵌入宮觀網絡的法派:明代道教與地方社會》)是這一趨勢的代表性成果。這部著作以明初高道劉淵然為主線,還原了劉淵然道派在官僚體制和不同地域的傳播擴展歷程,生動再現了明王朝疆域內波瀾壯闊的道教史圖景。劉淵然累仕五朝,足跡遍及多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明初道教的發展特點,是明代最重要的道士之一。在明代中前期,劉淵然及其傳人是在朝野甚有影響的道教團體。作者對這一明代道教脈絡的建立和流變過程予以了細緻梳理,不僅凸顯了劉淵然作為官道的政治內涵,還通過有关劉淵然的多元地方性記錄來展現明代道士「在地方和國家之間來回穿梭」(mov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national, p.5)的可能性。
為了精確地展現劉淵然道派道教活動的多重線索,王崗教授借用了「Lineage」的概念解釋明清道教實踐網絡。該詞大致接近道教研究中的「法派」或「道派」,代表了一種圍繞師徒關係的穩定傳承。明清史學者認為這種模擬父係家族的結構滲透到明清中國「幾乎所有有意識組織起來的後代群體」[1],《嵌入宮觀網絡的法派》一書展現了道教法派發展中的類似現象。學術界通過比較那些曾被忽視的字輩詩與現存的道士名單,已揭示了部分明清法派的歷史。作者更進一步使用了「宮觀網絡」(Temple Networks)的概念,為道教在地方社會扮演的角色尋得更為具體的場景。
本書除了導論和結論外,共分為兩個部分,分別對應「國家」和「地方」的層面,每個部分又各包含四章。
第一部分從制度化的角度來分析劉淵然道派。作者在第一章介紹了明代道教世系依據政治或道法等可能的劃分方式之後,在第二章充分論證了清微傳統在趙宜真、劉淵然一脈傳承過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明代初期,帝王推崇道教的禮儀和實用功能,從政策和制度層面對正一派予以了傾斜和保障。在此過程中,劉淵然一派同清微派、淨明派、龍虎山派及全真派漸生關聯,並在王朝道教官僚體制中發揮了作用。具體到劉淵然本人,他雖曾在身後被追認為全真和淨明宗師,並被部分近現代研究成果所渲染,但作者並未輕信。作者通過對教內外資料的細讀與對比,特別是對劉淵然傳記的史源學考察,系统論證了劉淵然的清微派歸屬。
按照「法派」的概念,能夠還原劉淵然清微世系的指征之一是字輩譜和弟子名單的吻合。作者通過比對劉淵然傳人和存世派詩,確定了以下派詩:「宜淵以道志,永德振常存;昭應通玄理,惟希最有成」(p.157)。這一總結有助於從明代官道的名單中發掘可能的劉淵然法派弟子,並重現他們基於宮觀的發展網絡。已知的明代至少六代弟子,遵循劉淵然的「國家」路線,服務於王朝的宗教管理體制,在與龍虎山等法派的競合中尋求政治資源。這或可視作劉淵然所塑造的法派底色。
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是關於齊雲山的個案,同樣用以說明劉淵然道派加強國家宗教正統性的作用。作者認為劉淵然的清微派傳人曾在齊雲山起到「皇室代理人」的作用,並幫助齊雲山道教達到鼎盛。其背後的政治動因是明世宗想要在明成祖確立的武當山之外,重塑一個宗教中心,獲得真武的護佑,以合法化他從皇室旁系中登基的政治權力。與此相對的是,以江南士人為主的文人群體卻強調齊雲山的文化特色,希望將之塑造成理想的士人山水,著意忽視或削弱其宗教意義。這與後文提及的茅山官道和全真的道教分野似有精神契合之處。
為了充分展示劉淵然道派與地方社會之間融合的多重樣態,本書的第二部分提供了四個詳細的案例,分別牽涉天津、江蘇、江西和雲南。天津與江蘇的個案分別依附於兩京的地緣結構,江西和雲南則呈現王朝腹地和邊疆的豐富變化。
天津天妃宮清微派的個案顯得系統而精巧。作者細緻梳理了天津天妃宮相關史料,揭示了一個在天后宮及當地的子廟中傳承有序的地方性劉淵然法派。這一支派始於劉淵然道派的第五代弟子李得晟,他曾在道錄司任職,與中樞關係密切,代表了天妃宮清微道士的「國家」面向。該支派的傳承與天妃宮密不可分。天津的地緣與商業活動使得媽祖信仰大盛,而天妃宮實為當地的信仰中心。清微派主導的天妃宮則通過道教儀式、廟會等活動深入天津地方社會生活當中,並逐漸掌控了多個子廟,形成了清微派的宮觀網絡。這是作者書名所稱「嵌入宮觀網絡的法派」的典型案例。
江蘇茅山是道教重鎮,具有層累的深厚歷史。作者基於對《茅山志》等資料的整理,勾勒出了劉淵然清微派在茅山的傳衍軌跡。他進而利用有限材料,對文士支持的全真宮觀和貴族、鹽商支持的包括清微宮觀在內的正一宮觀進行比較,深刻揭示了茅山所體現的明代道教結構。茅山與本書第二部分的另外三個個案相比,具有更加深厚的政治背景。作者注意到了茅山的「國家」面向,計劃進一步分析《茅山志》國家儀式內容。這將有助於重估劉淵然道派個案之間的細微性質差異。
相較於天津和茅山,江西的情況顯得更為複雜。作者聚焦明代江西淨明道的實態,分析了以許遜為首的「十二真君」崇拜、淨明道慶典、劉淵然淨明譜系的江西迴響、江西淨明道廟網絡以及地方香火崇拜等內容,形成了關於明代淨明道的新認知。作者認為,明代淨明道既指崇奉許遜、高彰「忠孝」觀念的道教運動,也指崇奉「十二真君」的江西地方崇拜,並沒有具體的道法傳承。(p.220)關於江西的淨明傳統與由江南(南都)孕生的劉淵然淨明背景的相遇,作者給出了李鼎等信教士人參與的合理推斷,暗示了一條由江南向江西回溯的路徑。
雲南是一個更晚的例子,甚至已經略微溢出了本書所處理的時段。面對雲南這一劉淵然曾生活與傳道的重要區域,作者選取了昆明虛凝庵作為分析對象。他首先呈現了劉淵然清微派在虛凝庵的穩定傳承,繼而討論該派與全真龍門派的關係。在本地宗教傳統、文士社群、軍事家族等影響力量的拉鋸下,逐漸主導虛凝庵的龍門派和潛伏的劉淵然長春派之間似乎呈現一種彼此消長的狀態。誠如作者所論,這一個案有助於細化明末清初龍門崛起過程中的多元地方路徑。
總體而言,《嵌入宮觀網絡的法派》延續了王崗教授嚴謹樸實的學風和從制度史把握道教的思路。全書以精嚴的考據勾勒出一幅明代道派發展的世系圖,並將這種世系的構建還原到明王朝政治制度架構和地方網絡當中。這一道教世系在協調宮觀、節慶、地方社群等地方網絡與國家之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換而言之,作者以劉淵然道派為例,綜合使用社會史、人類學等方法,切實論證了道教作為明王朝國家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際上扮演了不容忽略的社會角色,在社會整合、民眾教化、文化熏習等方面均有實質性貢獻。該書增進了我們對明代道教自身及其社會功能的認知,「道教主張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和文明力量,起到在地方組織和中央國家機構之間調解的作用,並為地方社會和國家賦予意義和合法性。」(p.29)除了視角與方法帶來的啟發,作者對史料的搜集與挖掘堪稱典範。例如,前述對隱晦的字輩詩的考證細緻入微。如作者對南京小觀清江道院中僅僅兩代弟子字輩的考證令人印象深刻,雖然很難就此定性宮觀道法的長期傳統,(p. 254)但毫無疑問扎實而具體的文獻工作有益於明清道教史研究的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劉淵然法派」之名有助於認知這一道教團體,但這一法派內部是鬆散而多元的,存在複雜面相。對於不同區域、階層、身份的道士來說,即使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法術和派別傳承,也可能會不遺餘力地利用劉淵然重構個人的宗教身份。一個本書尚未注意到的例子是劉淵然終老之所南京朝天宮西山道院的道士李振卿。李振卿自號「冶城西山道院清和羽士」、自稱「嗣法弟子」,[2]在正德、嘉靖年間所編集的《薩真人戒行實錄》中,曾記述了一條由薩守堅而傳於自身的師派,在西山道院處於核心地位的趙宜真、劉淵然被巧妙地穿插在這一神霄傳統中。這一宗派敘述有可能對道士在現實當中的道法傳承與身分認同產生影響。又如劉淵然在地方科儀本當中的閃現,很可能曾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借用」或「挪用」現象,即借助劉淵然的政治與教內身分重塑或強化地方宗教傳統的正統性,即便在劉淵然曾經駐紮的核心區域這類重塑依然存在。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地方道士的行事邏輯並非全由道派框定,道法、派字歌、師徒傳承等界定道派的要素都有可能屈從於更為現實而靈活的政治和經濟需求。
在劉淵然被不斷轉化和利用的過程中,他在某種程度上被抽象為一種明代道教政治的合法符號。幾乎沒有任何地方的劉淵然故事是脫離了國家隱喻的,即使是邊陲之地的雲南。至於這一抽象符號與地方道派發展的聯繫,是單純停留在派字歌中,還是可以深入道法、組織甚至精神的層面,則屬於需要進一步考量的問題。區域和時段可能是影響劉淵然法派穩定性的因素,劉淵然弟子突破清微傳統的建構其實已經表明了這一法派傳統並非固定不變的。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個案之間的孤立性逐漸增強。這與此前學界深入剖析的明代龍虎山等個案「Lineage」的構建方式之間有所差異[3]。
更為安全的做法或許是將「法派」的概念進一步固著到儀式、經典等更為具體的標準上,使法派在組織模式之外持續承載思想的要素。以這樣的標準重新審視地方化的劉淵然故事,就會對「嵌入」程度有更為豐富的認知。事實上,在淨明傳統強大的江西,劉淵然道脈是否曾成功「嵌入」值得疑問,因為除了零散的文本上的證據,在廟宇網絡和儀式中都很難窺見劉淵然的具體影響,更遑論實踐中的道士傳承了。而在天津天后宮的個案中,那些有能力依附中樞政治力量的道士和他們或許不大貼近中樞的後輩,在國家和地方之間的抉擇可能有不同的傾向。已知的有限資料尚不足以呈現這種細節化的歷史變遷,以體現地方案例中可能存在的「劉淵然認同」的衰減過程。這使得劉淵然法派傳承在地方語境中似乎變成一個穩定但模糊的既定事實,而掩蓋了其間的矛盾、挫折和衰變。就目前的資料而言,將劉淵然三代以內的弟子視為一集中的「法派」是較為穩妥的做法。此一時段的劉淵然弟子更集中於政治中樞,彼此對道派資源的汲取方式更為一致。此時段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可能是這一法派圍繞兩京、名山等政治地標的流動。書中並沒有關於劉淵然南方大本營南京的專章,實際上南京西山道院和道錄司同樣是法派展開初期的重要據點,並與更為龐大的新興道官集團彼此競合。當然這一複雜的道教政治圖景僅依靠劉淵然法派來展現可能會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綜上所述,相信本書對明清道教世系的爬梳,尤其是劉淵然法派歷史的系統化呈現,可以生動地展現道教在明代社會中的結構性功能。更進一步說,該書的嘗試實為理解中國明清以來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增添了來自道教脈絡的細節化案例。作者使用的法派等概念,可以同業已成熟的家族、政治世系、佛教「法緣宗族」等概念展開比較。此前廣受關注的宗族經濟因素、共同儀式活動等,在明代道教法派發展方面是否有類似的反映,或將幫助進一步釐清道教法派的構成要素。在此基礎上,作者所期望的道教史與明清史研究的交流,包括宗教政策、社會結構、地域社會、央地關係等廣泛議題的對話,將會獲得更為堅實的基礎。
注釋
*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THAD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陶金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 賀晏然係東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褚國鋒係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博士後。
[1] Timothy Brook, “Must lineages own land?”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0, no. 4 (1988): 79.
[2] [明] 李振卿:《薩真人戒行實錄》,南京圖書館藏嘉靖二年刻本。
[3] Vincent Goossaert, “Bureaucratic Charisma: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Institution and Court Taoists in Late-Qing China,” Asia Major17 no. 2 (2004): 121-159;曾龍生:《道法與宗法:明代正一道張天師家族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4 (2018.12): 711-753。
相關鏈接:
(内容来源:道教和宗教史研究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