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1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的“植芳讲座”系列之“现代中国诗学的发轫——鲁迅1907年《摩罗诗力说》及其他”于光华楼西主楼1401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教授、澳大利亚东方研究会主席、澳大利亚国家人文学院院士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教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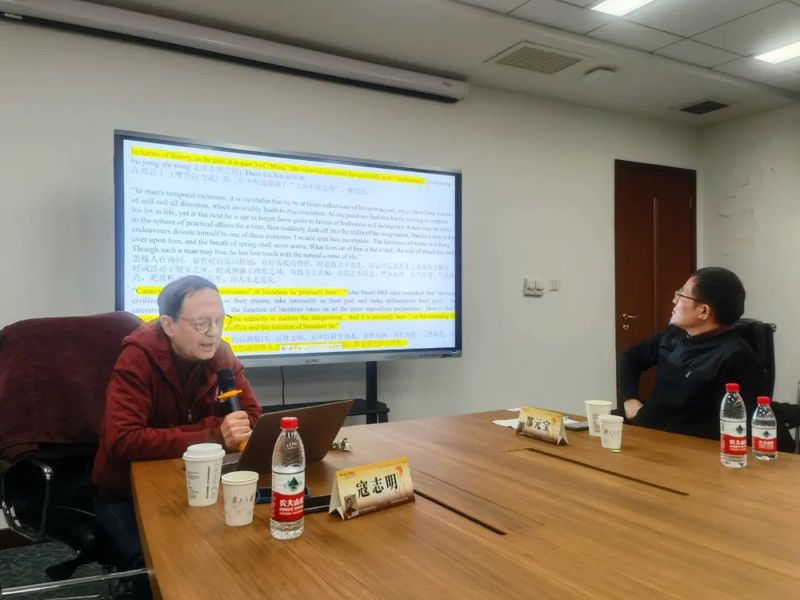
郜元宝教授首先介绍了寇志明教授的学术经历和成果,尤其是他自70年代末与中国国内学术界的密切联系,如在北京大学作为高级进修生师从王瑶教授与孙玉石教授,在编译局与杨宪益、戴乃迭等学者合作的经历。郜教授回忆了自己在1998年于墨尔本大学与寇教授的相识,以及寇教授作为复旦大学“植芳讲座”教授与复旦的学缘。郜教授对寇教授的著作The Subtle Revolution: Poets of the “Old Schools”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The Lyrical Lu Xun: 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诗人鲁迅:其旧体诗研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年)、Warriors of the Spirit: the Early wenyan Essays of Lu Xun(《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做了简要评介,介绍了寇教授自博士论文选题以来长达五十年的对鲁迅早期文言的研究兴趣,以及他目前已完成《摩罗诗力说》全篇英译注的工作。
寇志明教授的讲座首先分享了他的研究历程:他自80年代于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开始关注《摩罗诗力说》,至新南威尔士大学任教后开设了“中国诗与诗学翻译理论”、“著名文人书信的翻译”这两门关于翻译的课程。在授课中,他对翻译的观点也发生变化,从最初追求将19世纪的文言译为19世纪的英文风格(style),发展到后来认为应该保留原意而放弃风格,近年来又转回归最初的观点。因此,在翻译鲁迅早期文言时也追求保留它原有的诗韵,故如曾经修改旧体诗的英译稿那样,多次且大量地修改鲁迅早期文言四篇的译文。在讲座中,凡引用鲁迅原文时,寇教授常常分享他对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英译。
寇教授重视《摩罗诗力说》的写作背景:此文是鲁迅1907年在东京放弃医学后所作,因此,寇教授将《摩罗诗力说》视作鲁迅新文学生涯的开端。
寇教授对《摩罗诗力说》的内容和理论做了梳理和分析。《摩罗诗力说》的标题来自曾被封为英国桂冠诗人的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对拜伦(Lord Byron)的蔑称。骚塞称拜伦为“受恶神摩洛(Moloch)和彼列(Belial)精神影响的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首领”,但鲁迅却采用梵文神名Mara把拜伦一派的诗译为“摩罗”诗,而非更为常用的“撒旦”。鲁迅反对用一般人认为是恶神的名字来译,是因为他肯定了拜伦,并视之为呼吁全世界被迫的人反抗现状和伸张正义之人。

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开篇即谈到世界的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印度、以色列和伊朗)逐渐成为衰落的“影国”,他将这与他们的“文事式微”联系起来,随后强调了文学“新声”在提振人民精神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寇教授认为,如此一来,《摩罗诗力说》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预言了后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谈到刘勰《文心雕龙》以及屈原的内容和立场,随后,转向从尼采(Nietzsche)和果戈里(Gogol)汲取灵感,但更主要的是从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那里汲取灵感,并通过他们影响到的各个作家和诗人去追寻他们对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以及俄罗斯的影响。最后,鲁迅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öfi)给与非常高的评价。
在理论上,《摩罗诗力说》第三章强调了“文章不用之用”。他写道:
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
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寇教授探讨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目前鲁迅研究界对《摩罗诗力说》的研究历程。寇教授认为,鲁迅早期论文所用古文的难度无疑阻碍了读者的阅读,因此先后被包括洪桥在内的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小组、夏志清眼中“最优秀的鲁迅传记作者之一”王士菁、南京大学中文系赵瑞蕻等先生翻译成白话文。
鲁迅研究界对《摩罗诗力说》有不同的看法,如赵瑞蕻先生称之为鲁迅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寇教授认为,在此之外《摩罗诗力说》另有深意。鲁迅在文中重新评价了中国文学遗产,大体概述了十九世纪东、西欧诗歌,批判性地介绍了拜伦、雪莱及普希金,高度评价了莱蒙托夫和密茨凯维奇,并将裴多菲奉为经典;他解读了“恐怖主义”,并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学做出了设想。他赞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观点。王德威教授讨论如何使用“文论”这一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文学理论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打破西方文学理论在全球的话语霸权的必要性。他提出,有必要在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等作品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论。从王德威对鲁迅早期论文思想的极大兴趣中,足以看出他发现其中所表达的思想对建立一种“新的中国诗学”颇有助益。
随后,寇教授分享了他对《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研究的观点。他介绍了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教授从1972年10月到1995年8月分24期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ノ-ト》(《〈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证笔记》)系列文章,这些研究追溯了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时参考的众多日本和欧洲文献的来源。鲁迅当时的资料来源众多,寇教授对这些著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
寇教授认为,如果说鲁迅年轻时写过一篇类似博士论文的文学文章,那它就是《摩罗诗力说》。对于这篇文论的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解释。赵瑞蕻教授认为,这篇文论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鲁迅因此可以看作该领域的奠基人;北冈正子则是从寻找它的材料来源的角度来理解它。寇教授则把它看作鲁迅文学生涯的蓝图。
有些中国学者对北冈正子的研究有看法,认为北冈正子“将《摩诗力说》当做一部翻译,甚至剽窃之作”,但北冈正子在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中已经探讨过所谓“抄袭”的问题,她写道:“我想补充一点,《摩罗诗力说》中关于‘恶魔派’谱系诗人的大部分章节内容根据的材料,我们都有。但《摩罗诗力说》的要义不是来源材料的使用能够总结概括。如果用现代学术界里流行的话语它可能会引起‘抄袭’的争议,但我此前用的很多例子应该已经说明过这一点。我要强调的是,鲁迅在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中追寻‘恶魔派’谱系诗人的方式以及他的论文所构建的并不是‘抄袭’。我认为要理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真正用意,恰好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读。另外,鲁迅选择和使用这些材料用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与依靠他人观点来明问题是不同的。”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摩罗诗力说》和鲁迅的其他早期文论受到中国及海外学者的重视程度。它们揭示了鲁迅早期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因此它们是理解鲁迅思想发展的关键,即使它们被认为是他的思想形成期也因此是不成熟时期的产物。
寇教授探讨的第二个话题,是如何处理在任何外文文本中都找不到的引文及其含义。如《摩罗诗力说》第四章对拜伦的总结评价“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曰,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无法在拜伦著作中找到这段“引文”。寇教授与美国拜伦专家莱斯利·马尔尚(Leslie Marchand)的通信也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它原来是拜伦明治时代的日本传记作家和翻译家木村鹰太郎的引文,木村1902年出版的《拜伦:文学界的大撒旦》一书第273页说拜伦在希腊战场上,第334页说拜伦在希腊去世前大约三个月与一位美国人的对话。拜伦在谈话中表达了去美国的愿望,但对美国没有像这样诗意的赞美,当时美国被欧洲进步人士看成是一个抵抗欧洲反动势力的年轻弱小国,也是古希腊民主传统的精神继承者。这种抒情“引文”虽然是学者和学术翻译家的难题,但对于鲁迅建立关于拜伦的结论点来说,在修辞上至关重要:“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鲁迅非常钦佩的拜伦,很可能同时也是鲁迅自己的一方面的形象:一个自由和人权的捍卫者;同时,在1930年代把他的名字借给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文化运动。
寇教授认为,鲁迅早期文论很长时间在中国国内受到忽视,与它们语言的晦涩难懂有部分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其中有一些有争议性的思想,比如尼采直到最近还被看作一个原始法西斯主义者,还有鲁迅对大众——或者那些声称代表人民大众的统治者们——坚制个人和少数群体权利的谴责。
寇教授认为,鲁迅的早期文论在文学和思想方面开辟了一个大胆的全新的方向:它们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政治中的某些思想元素,但又不是完全地反传统;它们在拥护西学和思想自由的同时,又拒绝将西方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的样板。可以说,它们为当时和现在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倡国际主义、自我反省以及鲁迅自己说的“剖物质,张精神”的思想。最后,寇教授又串讲了《摩罗诗力说》九个章节,并对其中他的解释展开详细的说明。
寇志明教授的专题分享结束后,郜元宝教授及在座各位同学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郜教授表示,可惜鲁迅早期的几篇文章是“抄袭”和“生凑”、是否不必太看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正如北冈正子所说,引用能否表达鲁迅自己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引用中有很多改译、选择,正是思想的体现。郜教授提示:北冈正子讲到裴多菲的时候,是通过匈牙利学者的帮助知道“绝望之于虚无,正与希望相同”的材源,但她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学者、翻译裴多菲的专家兴万生先生在1978就找出这句话出自裴多菲的书信集(这一观点1983年发表),可惜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不够密切,二人未必互相知晓对方的研究,但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北冈正子的发现。郜教授又针对翻译提问:寇教授将“新神思宗”译作new idealism school,但在引用“文学不用之用是涵养神思”又将“神思”译作“imagination”,那么神思究竟是imagination还是idea?寇教授认为,翻译要取决于上下文,词组的意思是上下文决定的。神思既可以是idea,也可以翻译成imagination。
在场中文系博士生李恒顺同学对寇教授翻译鲁迅早期文论的工作提问,包括(一)鲁迅翻译在“摩罗”和“撒旦”间的取舍,是否自觉。寇教授作出回应,表示“撒旦”是当时日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译法,因此是鲁迅自己专门使用了“摩罗”。(二)香港中文大学崔文东教授的研究推进了北冈正子关于前三章是鲁迅自己的话、第四章之后方有众多材源的保守判断,找到了前三章的材源。其中,如“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一段,《鲁迅全集》作“约翰·穆勒”,从其材源坪内逍遥阅、坪内锐雄著《文学研究法》来看,实为约翰·莫莱(John Morley)。同学提问,对这种新材源考,寇教授对《摩罗诗力说》的翻译中是否考虑修改和注释?寇教授表示,对这类问题的英译,应当加注释以说明。(三)对鲁迅文本中来源于英文文献,随后被翻译为日文再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字,应该如何英译?是否列出原文的英文,并根据鲁迅的语气再重新翻译,并将二者对照。寇教授表示赞同。
寇教授又调研了国内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培养中鲁迅早期论文处于经典还是边缘地位的问题。郜元宝老师又针对鲁迅为什么要把文言论文编入第二本杂文集《坟》中、寇教授英译《摩罗诗力说》等早期文言的目的及其目标读者、寇教授目前正在进行的《鲁迅略传及中、英、日文鲁迅研究专著述评》的工作计划和状态等问题,与寇教授进行交流。
最后,在场师生再次向寇志明教授的报告和郜元宝教授的对谈表示感谢,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